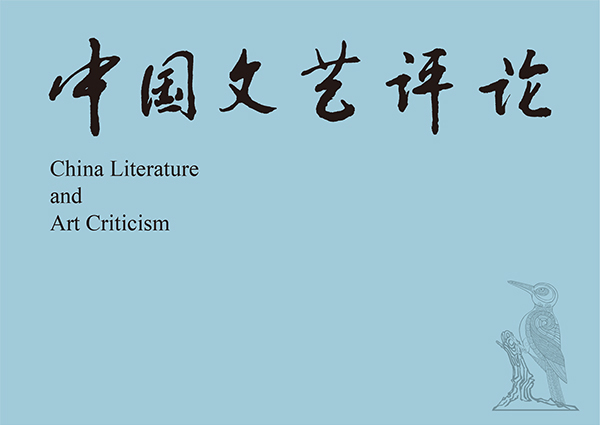
内容摘要:崇高是西方美学的重要范畴。音画对立作为影视音乐和画面关系中一种颠覆常规的艺术表达方式,其恰与崇高美学范畴不谋而合。影视借助音画对立手段可以揭示出二元对立的丰富美学内涵,如激情和淡然、痛苦与肃穆、空灵与充实等。从崇高美学角度出发,聚焦影视音画对立手法,分析崇高美学在影视创作中的妙用,进而探析崇高视阈中的痛感超越、思想超越、精神超越等对影视创作的美学启发,于今后国产影视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应不无裨益。
关 键 词:崇高 美学 影视 音画对立
一、影视音画对立与崇高美学的关联
“科学道德艺术乃圆满人格之三面”[1],它们涵盖了真与知、善与意、美与情的方方面面。其中,艺术陶冶情操,特色在于感化,因感化而养成好美之心。美,作为一种理念,其首先应是真的,但仅是真的理念尚不足以称为美;理念需通过美的形式外显。因而,理念不仅仅是真的,而且也是美的。一如黑格尔所言:“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理念”与“感性显现”相互承载:“美与真是一回事。也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但是这理念也要在外在界实现自己,得到确定的现存的存在,即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真,就它是真来说,也存在着。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3]鉴此,我们可以这样诠释影视作品美感表达的语义范畴:所谓“理念”,意指影视的“意蕴”,即作品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4],是统摄影视艺术作品外在形式的要核,乃最接近美的层面。在黑格尔看来,“意蕴”是“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5],即它并不直接呈现于观众面前,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而所谓“感性显现”,乃指影视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依托画面与音乐、音响等声音的组合表达,从而起到塑造人物、烘托环境、丰富情节的作用。
影视的音乐与画面关系主要分“音画同步(也称音画合一)”“音画分立”“音画对位”三种。当然,这是影视声音与画面的三种习常关系,“声画同步(也称声画合一,unison of sound and image)”“声画分立(independence of sound and image)”“声画对位(montage of sound and image)”之于音乐与画面关系的具体表达:声画同步乃指影视画面的视觉形象与其发出的声音同时呈现同时消失;声画分立乃指影视画面的视觉形象与声音互相分离,声音以画外音形式出现;声画对位乃指影视画面的视觉形象与声音从不同的方面分头进行,以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段表达同一含义。那么,这三种我们所熟知的概念运用到音乐与画面关系上,音画同步实指画中视觉形象与其所发出的音乐同时呈现同时消失,二者吻合一致;音画分立指画中音乐与视觉形象不同步,分别表现不同的内容,音乐和发音体不在同一画面,音乐以画外音形式出现;音画对位指音乐与画面对不同内容的表达虽分头并进但又殊途同归,从不同方面以象征、比喻等视觉修辞表现同一含义。除音画同步外,在某种意义上,音画分立和音画对位可谓“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对‘终极实在’之感受的形式。……艺术家灵感产生时的感情,是人们通过纯形式对它所揭示的现实本身的感情”[6]。
然而,长期以来,影视作品中一种偶露峥嵘但又不同于“音画同步”“音画分立”“音画对位”的音画表达方法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把这一有意味的形式称之为“音画对立”。当然,上升到整个声音层面,我们也可确立一种概念,即“声画对立(opposing of sound and image)”:影视画面的视觉形象与声音相反相悖,声音从与画面相反的方向来揭示人物心理,或渲染某种情绪,或暗示某种思想(如张艺谋2000年执导的《幸福时光》中,盲女吴颖回来发现自己工作的按摩房已不复存在的悲情画面,却配以热烈的欢呼声、鼓掌声和口哨声,以此揭示人物内心的焦虑、愤懑和迷惘,并暗示出关爱缺失的现实主题)。具体到音乐与画面的音画对立,实指画面的视觉形象与音乐分别表现不同内容,但两者在情绪、气氛、节奏乃至内容上相反相悖,对立表达。常见的表达方式有“以声代画、有画无声、声连画断、声幻画真、声动画静、声悲画喜、声喜画悲等”[7]。音画对立作为影视音画关系中颠覆常规的表现形式,往往在对立或相反的情感组合中呈现出较强的对比美感,也常常能营造出影片意蕴中的善与恶、生与死、有与无、动与静、悲与喜的对立交织。古希腊朴素辩证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美在于和谐,和谐在于对立的统一”;“和谐不是简单的整齐一律和绝对的平衡对称,而是在差异中见出协调,在不齐中见出整齐,在整体上给人以匀称一致、和顺适宜的感觉。”[8]也因如此,在塑造影视作品情感的力度、程度和强度上,音画对立所产生的情感内涵比一般的优美情感体验更胜一筹。因为,它激发的情感并非单向的情感(如非悲即喜式的),而是复合的情感(即悲喜交加式的)。此种复合情感乃对立与矛盾的交织并存。因而可以说,音画对立的影视表达手法更易激发出高于普通快感的快感,更能引起观众强烈的心灵悸动,而且,这种情感体验恰与崇高的美感体验不谋而合。
音画对立与情感表达的多样关系大致如下面的“音画对立矩阵图”所示:

二、影视音画对立的崇高美学范畴
叶朗先生在《美在意向》中曾经说过:“在西方文化史上,优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丑与荒诞等几对概念是涵盖面比较大的审美形态的概括和结晶,也是美学史上绝大多数美学家认同的审美范畴。”[9]事实上,优美与崇高作为一对重要的审美范畴,古今学者都给予广泛的关注:“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可以用来指代‘伟大’、‘恢弘’、‘雄浑’、‘壮阔’、‘庄严’、‘肃穆’、‘华丽’、‘铺张’、‘奢靡’、 ‘崇拜’、‘震撼’、‘诧异’、‘惊惧’、‘恐怖’、‘虚幻’、‘空无’、‘无限’,等等。”[10]
参照“音画对立矩阵图”,不难发现,崇高美学范畴的意蕴与音画对立或相反的情感表达有较大程度的契合。在某种意义上,影视艺术的音画对立手段可以成为崇高审美的有效表达方式。简单说来,优美与崇高审美范畴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从情感克制、痛感深入再到主体情感超越;崇高审美的运作机制是在痛感中超越,而超越则需建立在人们的觉悟之上方能实现。影视作品的音画对立手段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审美的功能:激发主体对痛感的自我超越,进而通过超越感而获得心灵的解放感,最终达至崇高——一种宇宙感、空间感和历史感的交融,一种对宇宙人生的无限哲思和深刻体悟。
1. 激情/淡然
“我这条命不管在哪儿活着,不管遇到什么变故,都会保持自我平衡,//都会像大树和野兽那样应付黑夜、风暴、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11]如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所抒发的气质一般,崇高的情感是激烈中的静谧,挫败中的胜利。当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和苦难的时候,崇高的激情会让人们从这些苦难中将自我悲苦、挫折转化为伟大。拉丁诗人维琪尔曾在史诗中咏述拉奥孔痛极大吼,但实际上发掘出来的希腊晚期雕像群中著名的拉奥孔并不是在狂吼,仅是微微呻吟。[12]这一雕像给人的印象是在极大的悲剧痛苦中保持镇定、静穆,就像“海的深处永远停留在静寂里”[13],如伟大而沉静的灵魂,尽管处于海洋般激情之中,静水流深处乃存在的真实,暗流涌动处实为深沉的热情。
电影《钢琴师》(The Pianist,罗曼•波兰斯基,2002)给予了我们崇高的审美体验,那是一种基于生命原初意识的本真情感。片尾处,落难的犹太钢琴师在德国军官面前弹奏肖邦(F. F. Chopin)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音乐情感由刚开始的卑微、平静、局促再到悲恸的隐忍,进而推高到激情的控诉。g小调的音乐调性时而忧伤、时而欣喜,使热情与悲情在音画中逆向交集,对演奏者复杂的情感进行了充满想象性的表述。该处的音画对立和情绪传达可对照图示如下:

《g小调第一叙事曲》是一首富有民族精神气质的英雄颂歌,它诞生于华沙革命失败的年代。当时音乐家肖邦流亡法国,乐曲中流露出他对国家的种种思念与情感;其音乐中所蕴含的“英雄性”和“悲剧性”也一度成为鼓舞波兰民族斗争的精神力量。在《钢琴师》这一段落的音画关系中,音乐是英雄的颂歌,象征反抗的激情,而与之匹配的画面却沉浸在冷蓝的月光下,四周的断壁残垣显然又是屠杀的烙印——废墟可谓庄严有力的存在,建筑受损后的残存部分显得既迷人又肃穆。音乐与画面,钢琴曲与废墟,分别代表动态的激情和庄严的淡然。钢琴师随着断续的琴声渐入深情,完全沉浸于音乐的空间氛围中:个体因自我和种族的一切苦难遭际爆发的情感,经由平静到炽热,再由炽热渐进沉静。钢琴的重音与冰冷的月光,一边是激情间隙的沉默,一边是有力的收束;当一切波澜归于平静之时,伟大便在静穆中诞生。
实际上,在《钢琴师》音乐表达激烈的情感之时,画面的冷色调乃是对音乐激昂情感的协调和克制,即巧妙地防止情绪过溢以至滥情。如暴力因愤怒而更加丑陋一样,情感也会因泛滥而失真。因而,在崇高美感的关照之下,影视艺术作品追求的真应是一种屹立于壮阔山河面前的真:一切伟大壮阔的景象都是激发人们产生崇高美感的形象,而它们必须是“真实而生动的”;因为只有真实、生动的情感内涵才能激发出真挚的感悟,进而生腾起崇高的美感。美是真的感性形式,崇高超越美,实是因为崇高不仅仅包含人间至善,它还倒映着一切苦难、挫败,汲取了人间百态作为丰富的养料——而这恰是真情实感体现于影视艺术中所依托的存在。另外,《钢琴师》中还有这样一处细节:月光透过窗户映照在废弃的房间里,钢琴师背对光线演奏营造出不可捉摸的逆光效果。在这里,柔和的逆光象征神秘,而激情的音乐与克制的画面则是对这种神秘的解读。很显然,《钢琴师》借助音画对立手段实现了饱满真挚情感的平静传达。
2. 痛苦/肃穆
崇高是一种“痛感审美和恐怖审美”,其情感来源于“心灵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14]。痛感在力量上比快感强烈,故是一种“最强烈的情欲”。其实,生命中的矛盾感就是一种痛苦,“所以在实在的世界里,只有较高级的自然物才获得一种能力,可以忍受和克服矛盾对立的痛苦”。[15]当人的生存底线被触碰时,被动主体就会产生痛感(包含恐惧、痛苦、可怕、危险等感受)。崇高并不指代一般意义上的难过、悲伤、苦恼等情感,它发端于痛苦,却需要激发出一种高于快感的快感。换句话说,崇高的伟大感悟是必须建立在痛感之上的。

《天地玄黄》剧照
电影纪录片《天地玄黄》(Baraka,罗恩•弗里克,1992)很巧合地和恐怖故事片《迷雾》(The Mist,弗兰克•达拉邦特,2007)使用了同一首来自英国乐队逝者善舞(Dead Can Dance)的音乐《撒拉弗众天使》(The Host of Seraphim,1988)。歌名以“撒拉弗”命名,撒拉弗是神的最高使者,代表爱和想象力的精灵,象征神圣与庄重。黑格尔曾说:“如果音乐要用艺术方式去表达最深刻的内容的内在意义和主体情感,特别是以痛苦的深渊为主要因素的基督教的宗教情感,它就必须在声音领域里找到一种手段,可以描绘这种对立面的斗争。”[16]在《天地玄黄》中,《撒拉弗众天使》的旋律开端运用了小七度和小二度的不和谐音程关系。这为画面的冲突和所抒发的情感提供了表达元素。其副歌部分的音乐调性呈现出由不和谐向和谐的递进关系,为主歌孤寂的女声独唱增添了一丝希冀。整首乐曲以管风琴为主伴奏器乐,女声的高亢诵唱和男声的低沉吟唱在管风琴雄伟壮阔的旋律音色中交错。正因如此,影片以壮丽山河和自然生灵所营造的空间氛围庄严而神圣。反观画面,《天地玄黄》则间断性地展示了世间的一片苦难景象,攫取了一些生命中的悲喜交织的真实场景:影像世界依次展现了拾荒者、流浪汉、孩童、妓女、日本舞踏表演者等小人物,同时也再现了垃圾填埋场、恒河火葬场、拥挤的地铁站及灯红酒绿的都市一角。概括起来,影片画面的意蕴内涵可归结为“贫穷”“落魄”“死亡”“肮脏”“沦落”“痛苦”等。该片音画对立与情感传达的对照如下图所示:

由此可见,《天地玄黄》的音乐所塑造的神圣、肃穆感是对一切苦难的超越,是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同时,画面运用升格镜头来加强其冲击力,使画面中的残忍性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怀,一如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绑缚在悬崖上被鹰啄食的普罗米修斯。因此,当观影者直面这些受难的灵魂,他们才有机会站在神灵大爱的视角下鸟瞰人间,纵使受难也是神性的显现。痛感的审美体验并非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情感,只有觉悟的人、勇敢的人、坚强的人、伟大的人方能化悲痛为力量,进而走向接受、理解与超脱。在本质层面上,良知未泯的人们对自然、世界、社会所犯下的罪行多能产生深刻的反省,亦能由此激发出自己对生命价值与生命尊严的感悟,进而激发出自我崇高感——它导源于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在影视作品的音画对立中,人们借此获得感悟大千世界的机会,在生命的矛盾交织中,痛苦与肃穆在彼此对冲中得以沉淀,人们的精神也得以升华,仿佛拥有了一种与巨大恐惧抗衡的尊严与力量——这是崇高对恐惧的超越,也是崇高自由意识的降临。
3. 空灵/充实
空灵与充实是崇高审美范畴的又一体现,是无限与有限的较量。康德认为,崇高的对象用在数量上和力量上的无限巨大,激发了主体的超越精神,主体由对对象的恐惧而产生的痛感而转化为由肯定主体尊严而产生的快感,这就是崇高感。[17]与形式主义的美学分析方法不同,康德认为崇高是“无形式”“无限性”的,正如“自然引起崇高的观念,主要由于它的混茫,它的最粗野最无规则的杂乱和荒凉,只要它标志出体积的力量”[18]。显然,康德倾向于主观意识的研究,强调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能力和超越能力,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之于此,崇高的核心意蕴乃追求无限,即用有限生命不断追求无限文明的进步,不为征服,而为实现主体对自我的超越,获得心灵的空灵与精神的充实。


《2001太空漫游》剧照
电影《2001太空漫游》(A Space Odyssey,斯坦利•库布里克,1968)中的古典音乐《蓝色多瑙河》与画面之间体现出艺术与科技、混沌与秩序的和谐对立,它们对崇高美进行了超越性演绎。这首由浪漫主义音乐家小约翰•施特劳斯所创作的圆舞曲节奏自由,旋律明快,洋溢着极富古典韵味的生命力。作为A大调乐曲,其音色欢快明丽,而其中的A大调小提琴则表现出自信、希望、和悦的真挚情感,流溢出期冀欢跃的氛围。不仅如此,片中的另一首歌曲来自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创作灵感源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同名著作——描写无神论者从唯心走向唯物的哲学思辨。全部乐曲共分九段,第一段以“日出”为题,于影片中与空寂、深渊、虚空的宇宙画面遥相呼应,将片头日出之景的震撼效果渲染得极为出色。雄壮而充满力度的音乐织体形象地揭示了人们对自然、宇宙的深刻感悟。也即是说:“人们必须在心中怀着升腾,为了能够创造出一个舞动的新星。”[19]混乱、混沌之初的宇宙乃一切之初始。太阳一出,即喻示慢慢孕育的文明;在此意义上,日出乃是人类由混茫走向明丽的里程碑。此时,音乐深情地奏响,配合画面迎来影片的开幕,进而在管弦乐的齐鸣中强力收尾。此处音画对立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空间感、宇宙感和历史感的交集,可谓对宇宙人生的无限哲思和深刻体悟。无疑,这能够达至影视艺术的升华境界,给人的感受极具空间感;也因有了空间感,人方感觉很自由;而因人感觉很自由,遂觉得很解放——美感也油然而生。

《2001太空漫游》剧照
日出、星空、宇宙乃世界之壮美之物,于无声息中蕴含生命的无穷无尽;美感就存在于它们的无限与不可琢磨之中。《2001太空漫游》的音画对立象征宇宙的空灵无限,又激发主体澎湃的情感。其音画对立与情感传达的对照可图示如下: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音乐与画面的表达对调。画面几无任何伴奏音乐。在辽阔的太空中,音乐的缺席彰显宇宙的真,也凸显“有与无”之间的饱满。正如韦应物《咏声》所论:“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在永恒静穆的世界中,静与动,无与有,空与实的对立才能使生命的热情彰显。西方交响乐意象宏大、内容饱满,热衷生命的蓬勃气息,可谓充实之艺术。相比之下,影视画面无音乐相对称,仅有地球、飞船映衬深邃的太空,彼此孤立绝缘,静故撩群动,空故纳万境,为空灵的太空营造一种动感,于是乎灵气往来。总而言之,空灵的宇宙画面与充实的音乐织体相配合,可给观众带来孤寂中的震撼感,从而创造出一个空灵悠远而又意味壮阔的宇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崇高的审美体验是介于充实、空灵二者之间的,是无限对有限的超越之美。
三、崇高中的超越性对影视实践的美学启发
基于音画对立所体现的崇高美学范畴的感性和理性认知,观诸影视实践,可以说,影视艺术的创作、欣赏、传播应该贯穿崇高美学的三个超越性,即痛感超越、思想超越和精神超越。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应秉承超越的精神力量,虔诚地塑造出艺术作品的生命美、心灵美、人格美,进而达到“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20]的双重审美境界。
1. 痛感超越:生命美
美学史家鲍桑葵曾经说过:“令人痛苦的现实并不是令人不愉快的”[21]。很显然,他所阐述的美学精神与我们的有关论述较为契合。其实,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埃德蒙•伯克的《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等都有论及崇高美与优美的差别。崇高带来的美不是平滑光亮、柔和精细的,而是粗糙不平,坚固而厚重的情感体验。崇高的审美基于痛感发生,但普通的悲痛并不能直接产生美感。事实上,人要化悲痛为力量,则需要先有一种深刻体验生命的自我觉悟,从而能主动、自觉地去理解和感受痛的来源,并在痛感压力下超越自己的情感束缚,产生自我生命的内省与反思。
生命的内省和反思过程会产生一股巨大的“自我纠错”力量,使人对自我、外物、世界的生命状态、生命处境产生联想和思考。这种纠错力量并非普通人可以承载的情感力量和情感历练。一如黑格尔对犹太人所描述的,“外在的不幸必然成为人类本身自在的痛苦”,但是,罗马世界还缺乏“内心自身感到这种痛苦和渴望”的“更高的规定性”,犹太民族的“历史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在于他们达到了这种“更高的境界”,即精神由于从作为它的分裂和痛苦的他在自在地反思自己而达到了绝对的自我意识。[22]崇高降落于世人之身,是要造就一个有觉悟的、勇敢的、坚强的、勤奋的、伟大的人,而在成为这样的人之前,必须如《孟子》所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因而,在痛感超越过程中,人往往容易犯错,也就因为犯错,方有改错自新的机会。当然,人应心怀悲苦怜悯之心,方能最终有所作为。之于影视艺术,崇高在痛感超越方面就是要把世间的一切大慈大悲揭示于外,喻示于言,从而为观众了解和感悟。自然,悲苦并不是直接被体悟的,而是被间接地感悟。“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23]当观影者在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中接受到恐惧、畏惧等负面情绪,并将痛感纳入自己的审美体验当中时,便会引发内省、反思进而产生纠错力量,直面自身的善与恶,正视自己言行的对与错,最终实现深层次的生命启迪和精神升华。
深入影视创作方面,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影视作品中植入“痛苦”的审美情感有何现实意义?纵观物质世界,“艺术时常被人们视为娱乐和消遣之玩物,于是其效果也就只能达到消遣和娱乐”[24]。在当下飞速发展的文化艺术产业中,部分以商业化为导向的批量化生产的工业化影视作品呈现出一种共性:千篇一律的剧情加上浮夸的特技。这类作品,无论时间如何沉淀,也不可能沉淀出深层的美学意蕴和审美反思。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表达出了大致相同的担心:在技术时代,不允许事物作为事物,而是把事物变成加工和统治的客体,以便为了人类无限增长的欲望和绝对的需要而开掘和耗尽这些事物[25];“语言到处迅速地被荒芜,不仅在一切语言的应用中损害了美学的和道德的责任,而且还是出自人的本性被危害”[26]。对此类以实现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工业化影视作品,观众猎奇的消费欲望一经满足,他们的观影趣味便消失于无形。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曾这样指出:艺术之变为文化的一部分,是艺术的堕落。[27]事实确乎如此。艺术的存在本来是要超越一切凡俗的,实为生命的出口;但艺术一旦被消费或仅仅为了消费,便难免堕落。因此,无论是艺术的创作者、欣赏者还是其他参与者,都应清楚地明白艺术此在为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这种牺牲若能基于崇高审美的体悟,既顺应时代发展诉求又能为人的生命之路点亮一盏明灯,则善莫大也。在这一意义上,人们通过具备痛感超越的影视艺术作品观照自我人生,才可能激发出人性中的慈悲,进而体验到具有改错功效的崇高审美快感。所谓“大慈大悲观天下之音”,即人的心中蕴含多少的悲伤和慈悲,方能观照出世间生命具有多少的悲伤和慈悲。痛感超越的影视艺术体验既是现实语境中的人们所急需,也是良知高扬的艺术家们渴望塑造和传达的崇高生命之美。

《黄土地》剧照
2. 思想超越:心灵美
在普泛意义上,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希望人回归本性之天真。丰子恺就曾写过《学艺术就是要恢复人的天真》的文章。艺术对人的真实影响,其实就是超越思想的束缚,使心灵返璞归真。当然,这里的真一方面指的是艺术思想中的情感真切。在崇高审美中,真情体验不是一种轻浮的泛情而是厚重的激情。无节制地挥霍情感中的喜、怒、哀、乐,只能被视为艺术作品中失了分寸的情感表现。因此,影视艺术所表达的情感应是激情而不滥情的情感状态——它们最终都应归结于真。真情是一种深沉的热情和克制的奔放,它让人感到自由和解放,使人思想升华,并产生美的结果。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认为崇高是一种蕴含思想力量的激情;这种情感是积极情感,表现为对自然、宇宙、山河的兴奋感和升腾感,映射出人们在自身生命中寻找思想超越的情感体验过程。[28]在《天地玄黄》《黄土地》(陈凯歌,1983)、《幸福时光》等众多影视作品中,音画对立的艺术手段都使观影者于不经意间触及此类审美体验。
在本质层面上,真亦是真理的艺术外现。人往往因为习惯而迷失于日常生活之中,被利害关系所困而久久不得所悟,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唯有艺术,搭建起人们与真理之间的桥梁。当除去一切习惯的迷障,天地万物的真相无不奇妙地尽显于人的眼前。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论及艺术作品及其本源问题时认为,真正的艺术应是一种本性的自由感,应让真理脱颖而出。[29]如上文所述,黑格尔在《美学》中也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美与真是一回事。由此可见,崇高是艺术走向心灵自由的必由之路,终极目的是追求艺术的真,从而祛魅。在这种祛魅的心路历程中,人们可以消解自身固定认知中的神秘性、神圣性和魅惑力,自在逍遥于世界,并以伟大的精神、丰沛的感情来解脱被时代、物质束缚的自由心灵。魏晋时期思想家嵇康提出的“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其实就是为了破解《周礼》影响下“礼乐刑政”对音乐的功利束缚,以解放艺术本有的独立性,进而启迪人们的意识觉醒。

《泰坦尼克号》剧照
事实上,《泰坦尼克号》(Titanic,詹姆斯•卡梅隆,1997)、《太阳照常升起》(姜文,2007)等可谓能够实现崇高的思想超越并达至心灵美的电影作品都暗循此道。影视创作者应深刻地发觉崇高之于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及审美之道,让创作回归真的本质,即从故事情节、音乐选择、画面设计、演员表演等角度入手,回归和还原艺术化的真,摆脱世俗化的束缚,积极激发人们向善向上的真实情感。无疑,影视作品中所能蕴含的真实情感越丰富,其所能承载和呈现出来的真实情感就越丰富,观众所能感受到的真实情感也就越丰富。倘如此,影视艺术作品就可以最终唤醒观众心中的崇高情怀,实现心灵的崇高审美与精神祛魅世界的关联。
3. 精神超越:人格美
宗白华说过:“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两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美’。”[30]中国艺术精神追求“为人生而艺术”。中国的崇高审美注重心中的灵性顿悟,依循人与自然亲和的方向。《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大美”其实就是道,人若想要寻找到美,就应行走于“天地”之间细心观察、寻找和体悟。“天地”之美在于其体现了“道”的自然无为的本性;人若能体验到这一点,心灵就可以不为利害所困,就能达到“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从而逍遥于天地、自然之间。相比起来,西方艺术精神更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西方的崇高审美强调以人的精神意识超越一切自然万物,因而更为注重人的自身超越意识的塑造。在艺术世界中,外部“天地”作为感情的客体,可以激发生命中的无限力量;崇高情感可以让人们体会到世界的宽广与无限性,并能激发自我精神意识走向解放与超越,形成自由意志对生命的共鸣,达至人生价值的超越和世界的终极追问。
虽然中西方的崇高审美观各不相同,但二者的最终艺术追求都是希望通过精神超越而获得美的人格塑造,因而二者又和而不同。艺术可以让人感悟真、善、美的本质,回归纯真,远离功利,体悟人生大美。优秀的影视作品和一般影视作品的差别,就在于引起崇高审美的感悟程度有高下之分。一切艺术创作都应发源于无涉利益的主观欲求,应关乎自然之道与生命的生生不息。艺术创作如此,艺术审美也应如此。影视艺术作为传播载体,终极目的实是为了实现“艺术”与“人生”之间的美好关联。

《太阳照常升起》剧照
概言之,无论是中国崇高审美中的灵性顿悟,还是西方崇高审美中的精神意志超越,都会对影视创作产生影响。影视艺术作品作为崇高的表达媒介,不仅仅服务于人生,也承载着对人的品质与性格的塑造与揭示。《礼记》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表明了人的技艺与修养之间的关系。优秀的影视作品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外在美的精巧绝伦,更应承载真情感的流露、真人格的外显和真人生的意味。“文艺不只是一面镜子,映现着世界,且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形相创造。它凭着韵律、节奏、形式的和谐、彩色的配合,成立一个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这宇宙是圆满的、自足的,而内部一切都是必然性的,因此是美的。”[31]
影视艺术的音画对立既是其自身表达的基础,也是其最终展示生命美、心灵美、人格美的崇高审美体验的必要前提。通过崇高审美的超越性(痛感超越、思想超越和精神超越),可使人超越自身的局限及物欲的束缚,使影视作品更为深刻,使审美人格更为圆满。在崇高美学的指引下,追求高格与有道德底线、艺术尺度的影视创作者和接受者一定可以自发以至自觉地感悟天地,最终走向影视艺术与人生大美的自由之路。
延伸阅读:
提质增效与升级换代:构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格局(饶曙光 李国聪)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