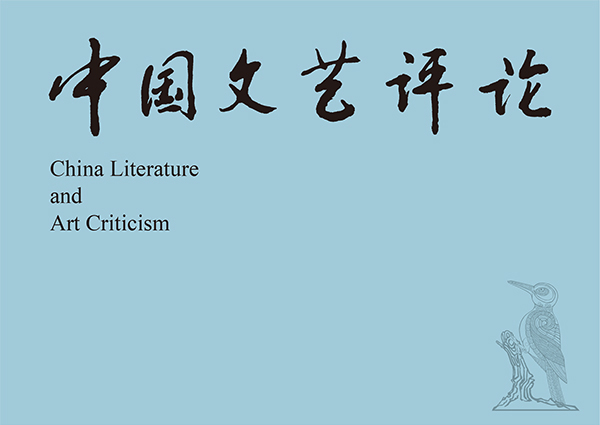
内容摘要:散文可以分为三种不同范畴的类型。作为一种非虚构文体,其区别于小说的根本在于真实性。散文的真实性是在事实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结合了判断真实和想象真实的一种艺术真实。艺术真实的本质和实现的重要手段在于想象。散文需要合乎艺术真实原则的想象。
关 键 词:散文 事实真实 历史真实 判断真实 想象真实 艺术真实
散文这一种文体,很难有准确而严格的定义,其内涵与外延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灵活性。换言之,散文的边界并不规整拘囿,而是有着很大弹性的。
一、三种散文
从散文的外延及边界来区分,这种文体可以有三种定义,也就是存在着三种散文。
第一种散文的概念,是一个最宽泛、最大范畴的散文,亦即与韵文相对应的文体——非诗非合辙押韵的文学作品,皆为散文。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或“文章”的概念。我们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叫“诗文传统”,常常“诗文”并称。古代的“作文”、科举考试的答卷文章,均属此类,即与“诗”相对的“文”。古典文学的初始源头应该是两种。一是从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号子、口头吟唱发展而来的诗歌,一是从古人结绳记事,在陶片瓦罐、龟甲兽骨上刻字记事发展而来的“文”或“文章”。前者更多地诉诸语言、口头歌咏,后者更多地诉诸文字表达、书面记录。这种最广义的散文,在中国古代是与诗歌历史几乎一样悠久的一种本土文体,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文体,具有深厚的历史与传统的因袭承递。

从根源上看,中国的散文其实就是最早的文字记录、上古记事。这个源头往下流传,形成了最初的陶文、甲骨文卜筮记事、青铜铭文记事,以至后来的《竹书纪年》《春秋》《国策》等史传记载和先秦诸子百家。这种宽泛的散文的概念,包含了除诗歌之外的其他各种文学作品,如史传、唐宋话本、变文、明清小说、小品,直至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小说、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等各种文体。对于这种宽泛的“文”或“文章”,并无定法或定规,其在创作时亦不论虚构非虚构,在行文上不务求整饬规矩、无需押韵。它是一种自由文体。这种散文,可以采用各种表现或表达形式,如日记、报告、书信、游记等,不拘一格。它的内容更可以包罗万象,挥洒自如。
第二种散文,即我们今日所谓之“大散文”、广义散文的概念。它包含了狭义的散文、报告文学、随笔、杂文等。或者说,除去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文学作品皆可归入散文一族。因此,这种散文包括书信、日记、游记、档案、回忆录、口述、访谈、调查报告、通讯特写等各种具有艺术性、真实性的作品。它与读者之间的阅读伦理基础应该是真实;或者,读者愿意认可并接受作品所写所表乃是真实可信的。报告文学作为由海外输入却被完全中国化了的中国特色文体,其基本功能在于记事、写人、书史、反思,基本上可以归入广义的叙事散文之范畴,因此也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或部类。而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创作,亦符合散文的基本特征及属性,大体上可被散文所包纳。
第三种散文,则是一种狭义的散文,也就是被我们通常所规约接受的散文的概念。譬如,我们在文学评奖中所规定的散文即为此种散文。这种散文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一般包括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在文体上说,它包含了随笔、杂文、小品文,但不包括报告文学。这种散文通常具有形神统一、作者主体性意识鲜明、介入式的主观化叙事及表达、真实性等特征。在我看来,散文须求真、拟真、逼真,要让读者认同为真实,一般不接受虚构、编造和杜撰。
二、五种真实
真实性是散文的一种基本属性。真实,也是散文的力量之所在。散文之所以能感染读者很好地影响读者,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读者相信作者所写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而不是编造杜撰虚构的。我不否认,虚构的内容和作品也可以具备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但是,那样的作品——虚构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命运及其心灵叙事,应该被归入小说范畴。说得更直白些,小说这种文体的作品同样有感染力,但小说与散文的根本区别正在于虚构与非虚构。举例来说,中国的四大古典小说都有真人真事的影子和底子,都是从历史上真实的人和事件中引申演义而成的故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对三国历史的人为演义和艺术化加工,对于历史上那些人物作者倾注了个人的好恶等感情,对人物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事件的环境氛围等都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水浒传》是对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艺术化讲述及描写。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众梁山泊(今山东省梁山县),举旗造反。随后四处攻略,波及河北、山东,先后攻略十余州军。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等进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时,被海州知州张叔夜袭败,宋江等投降。此事件为宋人话本所演义,元人施耐庵据此创作《水浒传》,流传至今。而对《红楼梦》的索隐、考据式研究,似乎都能在作者曹雪芹及其他历史人物身上找到对应或相似的故事。吴承恩的《西游记》取材自唐朝高僧玄奘西去印度取经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的事实。这些作品通过对事实和历史的艺术加工,最终演变成了一种虚构文本,亦即小说。

当然,关于散文的真实性,我们还需要做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我认为,客观上存在着五种真实,或者说,真实有五种表现形式或呈现方式。
第一种真实是事实真实(或事件真实)。一个事情或事件的发生,有其自然的过程。它是客观存在的一段历史、一个时间片段。譬如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八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事实。事实本身所具备的真实性,是一种原初的,未被书写、记录、描述或剪裁的史实。这种真实只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中,是一种本质真实、绝对真实。它是一条流过去的河、一段已发生的历史。我们人类可以试图无限接近或还原这个真实但却永远无法达致。
第二种真实是历史真实,就是经由时间的沉淀之后对历史对事实的一种记录、记载或叙述。所有已经发生、已经过去的事情都是历史。对于这些“历史”事件、事情的记录、叙写,必然需要借助语言和文字,也就必然地要经过人的思维的剪裁过滤。历史记录者基本上需要发挥个人的主观性,运用想象等形象化思维,对“历史”竭力进行复原,努力写下真实准确的历史。而在记录和书写时,作者还会多多少少地加入个人的主观情感和倾向性,于是便会处在官修正史、外史、野史、稗史等之区别。在史书、文献中所表现出来的事件真实性,就是历史真实,譬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这是一种记录真实或叙述真实。可以说,历史真实只可能且永远只能无限接近事实真实或本质真实。运用语言文字或其他载体形式如音频、视频等所记录下来的历史,都是历史叙事、历史真实,即便是在今日,我们可以采用摄像头、高端的3D技术等实现更加完整准确的记录,但这种记录或叙述必然要受到介质本身有限性的局限,受到记录角度、方式、剪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永远无法进入同一条河流,这便决定了我们永远无法百分百准确地反映事实真实。尤其是人类文明早期的记录,更是掺杂了大量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都是将真实的现实与人类的各种想象、虚构乃至虚幻的联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这一类的历史真实实质上存在着大量的虚构成分,可信度并不太高。而即便是记录离作者最近时期的历史——如司马迁记述秦汉历史——也必然会受到作者的价值观、历史观、主观倾向性的影响,难免掺杂进个人的一些主观因素,因此尽管其可靠性和可信度较高,但也多少会存在一些不足或缺陷。中国历史上的传统都是由后一朝代主持撰写前朝历史往事,朝代取代者是胜利者和历史话语的主导者,必然要按照于己有利的叙事方式来叙史记事,凡是于己不利的事都会尽可能地避讳或隐去,因此这些历史记录所体现出的历史真实也必然是有限的或受限的真实。
第三种真实是判断真实,就是经过逻辑推理、价值评判,确认为真实的内容。这是一种可以证明的真实。与其相对的便是可以被证伪的虚假。因此,这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接近本质真实、客观真实。

第四种真实是想象真实,就是作者运用想象构筑起来的内容或世界,它既让人清楚地知道这是作者的主观想象和心理映像,但却能感觉可信、真实。因此,想象真实其实就是一种主观真实、心灵真实。它呈现的是心灵的真实世界,是心灵叙事。譬如,何其芳《画梦录》中收录的一系列独语散文,那是作者的心灵独白,作者的主观想象和自言自语。他想象着“有一所落寞的古老的屋子,画壁漫漶,阶石上铺着白藓,像期待着最后的脚步”——这便是他神往的一种境界。[1]鲁迅在散文集《野草》中所描述的诸多场景和人物,往往是作者主观情绪化心理的投射,是一种心理真实。《影的告别》以影子的口吻,讲述他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彷徨于无地”的情状,他愿意独自被黑暗所沉没,而放他人都到光明的地方去。——这个影子的形象,实际上投射了鲁迅的人格理想和抱负——“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这样的战士》描述了一位面对无物之阵举起投枪的战士,这显然也是作家人格化的对应物和形象。[3]换言之,这样的战士正是作家的一种自喻、自况或自比,他是作家想象出来的真实形象或自我。宗璞在《紫藤萝瀑布》中写道,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它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4]……这些段落几乎都是作家的主观意识和主观想象,但却是由真实的紫藤萝花架所引发的,令人感觉真实可信,如睹实物,感同身受。而在张守仁的《林中速写》中,热带雨林中的各种树木花草在他眼里都变成了一个个可触可感可知的对象,万种植物和动物和谐共生,相互依存,共同绘就了一幅优美绝伦的画面。作者感觉“在这里,每一瞬间,都在发生亿万次的新陈代谢。腐烂与新生、繁荣与枯萎,都在这生命的大舞台上演替。这里有最美妙的天籁,这里有最丰富的色彩,这里有最生动的形象。而当暴风袭来,林海枝舞叶涌,俯仰起伏,万千树干就是万千根摇曳的琴弦,弹奏出惊心动魄的交响乐;云雾涌来,一切淹没在白茫茫的浪涛之下,变成一片摇摆晃动的海底森林;但当热带雨倾泻过后,太阳重又照耀,亿万叶片上的水珠,闪烁出亿万颗晶亮的星星,炫人眼目”,因此“只有用一种不分段、头绪有点混乱的文字,才能充分表达出杂乱成一个板块的整体感受”。[5]这些描写正是作者主观想象的真实。由此可见,想象真实指的是作品中建构的世界、生活内容及空间基本上是从现实出发想象的产物,是作者的心灵映照或映像,但它们同样是真实的。
第五种真实是艺术真实,就是借助语言文字建构起来的真实。这是一种审美真实、接受真实。作者所写的内容,在读者读来,感觉或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同时读者在这种接受认识的前提下,受到作品内容的感染或感动。因此,这是一种诉诸读者阅读感受的影响力真实。它由作者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来建造,需要在读者的阅读中检验和完成。譬如朱自清感动了几代中国人的《背影》,追忆的是当年“父亲”坚持亲自到火车站送作者上车,爬下月台穿过铁道去给他买桔子的情景,父亲因为肥胖,在爬上月台时特别吃力,让作者感动落泪。读者在阅读时,跟随着作者的描述,仿佛回到了当时的现场,仿佛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执著和认真,也跟随着感受到了父亲的一颗慈爱之心,从而唤醒或激发了相似的记忆或想象,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高度认同作家的所叙所述,达到了一种审美接受同频共振的效果。——这是一位父亲的背影,用全部心思关爱呵护子女的父亲,他的背影令人不忍直视。也许岁月不居人生易老,但那些崇高的、与生俱来的爱却能穿越时空,时时敲打读者的心扉。《背影》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道出了普天之下每一位子女共同的心声:感恩父亲,祝福父亲!龙应台的《目送》则是以一位母亲的视角,注视着孩子一个脚步一个脚步的前行与成长,她目送着幼小的孩子第一次上学,“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孩子16岁时她到机场去送他赴美,眼看着他的背影在排队的人群中一寸一寸地向前挪,一直在期待着他的回头一瞥,但他却没有。孩子一次次不断地远去,只把背影留给了母亲,这使作者意识到父女母子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然而同时,她又发现了另一种背影和目送,那就是父亲的背影和对父亲的送别。父亲终于病倒,生活无法自理,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头低垂至胸口,排泄物淋满了大腿,而作者还要赶往机场回到台北上班,她只能目送着护士推着他的轮椅消失在自动玻璃门后。而最终,她面对的是父亲的棺材,目送他被送进了火化炉,“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6]这些目送的场景足以勾起读者相似的想象与回忆,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我们目睹的是自己最亲最爱的人一次次的背影远去,在他们身后总有我们深情凝望与注视的目光。从这些目光中我们不仅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自己的亲人,更看见了人伦至情与人间至爱。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是一篇怀念母亲之作。在儿子双腿瘫痪以致情绪无常之后,已然病入膏肓的母亲还在苦撑苦熬,只为多陪伴安慰儿子一些些。为了给儿子散散心,母亲一再提议去北海公园看花,就在即将成行之际,她却突然发病并就此溘然长逝,只留给儿女轻轻的执著的劝勉“好好活着”。作者在秋天和妹妹终于去北海看了菊花,也终于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7]这是天下儿女共同的心痛,共同的领悟,对于父母慈爱之心深切的体悟与感恩。因此,这些短文之所以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振,正是由于其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和表达。
散文所具有的真实性应该是一种艺术真实,它能够让读者认同、认可并接受作者所写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不是凭空虚构、杜撰编造的。如果作者直接告知读者自己所写的都是虚构的故事,那么读者是不会认同这是一篇散文。当然,艺术真实可以包括想象真实和历史真实。它既可以是历史性的叙事与记录,也可以是主观性的叙事或表达。从这个层面上看,着重表现历史真实的散文似乎可被称为叙事散文,而想象真实、思想真实的散文大致上可以归为抒情或哲理性散文。散文所具备的艺术真实应该首先不违背事实真实、判断真实的原则,但绝不是对事实真实的亦步亦趋或对判断真实的简单转述。它是历史真实、想象真实和判断真实的统一。散文的真实不能简单地适用证伪标尺,因为作者的心灵真实、思想和想象真实是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
三、一种想象
有人认为,文学是虚构的艺术。我不认同这样的论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想象的艺术,是更多地借助于形象思维的产物,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虚构的艺术或被全部装进虚构艺术这个筐子。因为,散文和报告文学都是追求艺术真实的文体,通常都不允许或读者也不会接受虚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申,文学是运用语言文字、发挥想象、表现现实或心灵生活的艺术。有人说,文学都是骗人的,如果从文学都是想象的产物这一角度来看,这一说法并无大错。文学,包括散文、报告文学,都需要发挥作者的主观想象力。想象力高下是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区分想象与虚构这两个概念。虚构基本上可谓是无中生有,而想象则大多为有中生有。虚构的内容可以由现实生活、社会事件、历史往事去生发、推演、演义,也可以毫无所本毫无所依天马行空自由驰骋。前者更近写实如《三国演义》,后者更近魔幻虚幻玄幻如《西游记》。散文不是虚构的艺术,但允许并且需要丰富的想象。这些想象皆基于真实,皆合乎想象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准则,它在读者眼里都是真实可信的,因此都具有感染力。认为散文要求具备真实性就否认了其可以且需要想象,这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的观点;而认为散文是想象的艺术因此便可以随意虚构编造,这是一种破坏散文文体个性乃至摧毁散文合法性基石的观点,它最终会给散文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小说化散文和散文化小说这两个概念。冰心的作品《小桔灯》有时被归入散文,有时又被归入小说,因为读者在阅读这篇作品时的感受也是模棱两可的,认为无论是把这篇作品视为散文或小说,其艺术的感染力都是相近的。换言之,读者已然不在乎这篇作品的文体属性。事实上,有许多作品对于读者的阅读审美接受而言,其究竟是否具备真实性,究竟是否真人真事或是作者虚构杜撰的人和事,其区别意义并不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小说采用了散文化的手法或文笔,譬如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的许多小说同他们的散文风格相似,形散而神不散,文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行文简洁明快,注重氛围的渲染及环境的描写等等,如《边城》《荷花淀》《羊舍一夕》《受戒》等等,即便当作散文来读,也是趣味盎然值得回味的。这大概就是散文化小说。而像李修文散文集《山河袈裟》里的许多篇章,则采用悬念伏笔设置、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的小说手法,譬如他描写自己深陷困境同一群修船民工同困一处时的相濡以沫彼此搀扶的动人情景;他刻画的一只备受主人关爱的猴子在主人不幸去世后,自觉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职责……这些情节都带有传奇色彩,似乎都有小说化的痕迹。毋庸讳言,在许多情形下,一篇作品或一个情节细节是否虚构,存在着众说纷纭众口难一的情形,即便是依凭读者的阅读审美接受来评判,也很难作出泾渭分明的明确判断。这些模糊的混沌地带,大概证明了散文与小说的边界有时并不明晰。
《一个人的村庄》中作者刘亮程“虚构”了一个在村里游荡的闲人,他不问耕耘稼穑,只关心人们忽略的两件大事——日出和日落。这个闲人以及这个闲人的行为似乎完全是作者主观臆造出来的。但是,他所代表的正是作者的一个主观意象、一个理想人物。这个人物是心灵的产物、心灵的映像,它符合想象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原则,读者在阅读时也接受其为真实可信的,也相信村子里可以存在着这样一个“闲人”。庄子的寓言,有许多极其丰富曼妙无边的想象,如鲲鹏万里、庄周梦蝶等,都可谓是作者主观臆造出来的想象真实,其作用于读者后便表现为艺术真实。这些内容不能简单地被贴上虚构的标签。十多年前,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树儿发表了一篇感人泪下的作品《娘啊,我的疯子娘》,影响甚广,后被改编成电影。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心理上都默认了这样的前提:作者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亲历亲感的,因此我们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据说,格致承认自己的一些“散文”作品是虚构的。有些评论家对此不以为意,有些则因此对格致散文的评价大打折扣。我认为,读者在阅读格致作品和《娘啊,我的疯子娘》时,受到了真实的感染产生了真切的共鸣或其他感受。这种影响力是基于艺术真实的基础。如果读者得知自己所读到的内容都是虚假的、虚构的,那么,他们的共鸣或其他感受便受到了一次破坏性的威胁或损害。换言之,名为散文而作者最终却承认其为虚构,这实际上是对这些作品的一次颠覆或解构,也是对读者阅读接受的一次颠覆。散文倘若丧失了真实性,其力量必将大受折损。正如《娘啊,我的疯子娘》改编成电影后感染力大不如原作一样,观众很少会将故事电影认同为真实认可为真人真事,而以真实见长的纪录片、纪实片却可以带给读者更深切更强烈的感动和感染力。我曾经询问过《娘啊,我的疯子娘》的作者,他说自己并无这样一位疯娘,但他有一位疯了的舅妈。他的写作有一些想象加工,但基本事实是有的。应该说,如果我们将这部作品视为散文,评价无疑会很高,当年我和诸多选家都在散文选本中收录了这篇作品即是明证。但是,如果我们将其定位为小说,那么,对其的评价则无疑要打对折。
今天,在文体边界不断被打破、穿越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申散文文体的尊严,这就是真实性原则。散文的真实性是在事实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结合了判断真实和想象真实的一种艺术真实。艺术真实的本质和实现的重要手段在于想象。散文需要合乎艺术真实原则的想象。散文应该遵循艺术真实的准绳,应该带给读者真实的感同身受和心理共鸣。真实性是散文的力量所在,也是散文的力量之源。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