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特别策划“理论探索”专栏刊发如下2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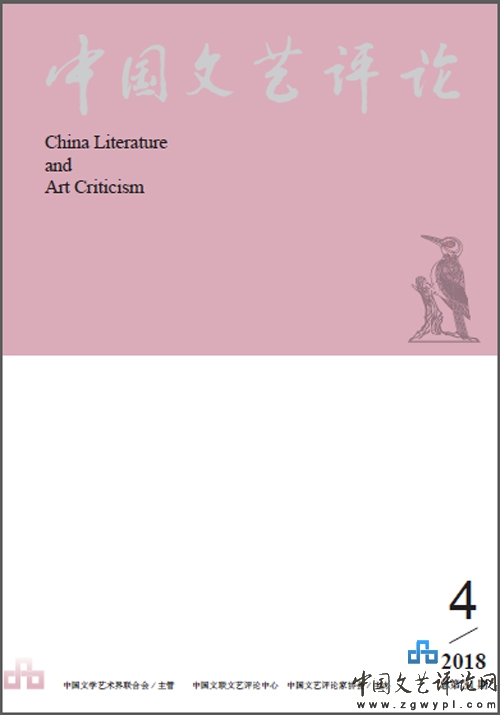
内容摘要:作家对生活世界越有自己完整的判断,就越能从纷繁杂乱的各种价值中形成独有的发现。小说反映社会反映生活是个批评的概念,而写好人物写活人物才是作家的看家本领,作家当以看家本领优先。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内涵的发现是通过所写人物及其关系而感知到的,越鲜活的人物越有助于读者感知故事的社会内涵。但是如果作家将批评的概念当成写作遵循的不二法门,渴望反映社会和反映生活的主观愿望优先并压倒写活人物,则小说的社会内涵就会变得干涸和枯萎,其美学趣味就要大打折扣。
关 键 词:生活世界 发现 《下广东》 奈保尔 改革开放

寒假得闲,断断续续读罢村水的小说《下广东》,开始读得很不畅顺,曾经一度放弃。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小说文本确实存在不够流畅的瑕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小说名声在外。连研讨会都在北京开过了,况且小说前序加附录共有五篇之多,我再来谈论,恐是多余。作者固然欢迎批评,多多益善,但坊间的评论多到一定程度,或属不甚正常。我也不愿再加油添醋,尽管我觉得小说故事提出值得我们再三思索、追求答案的问题——例如怎样理解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怎样理解小说写时代社会和写人的关系?但我又怀疑谈论这些连自己都没有答案或难以论定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意义。所以,念起提笔之事就犹疑不决。只是30万言的长篇读到最末,书中有一篇《告新桥同乡书》。它改变了我的犹豫不决,作者对写作的雄心鼓励我将自己的阅读感想连同与其相关的问题一并写出来。有的批评说作者是“无厘头”作家,因为语言风格多似“无厘头”,但整部作品而言,它犹是枝节。“无厘头”的背后有认真执着,作者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想为三十余年的社会变迁留下浓墨重彩。作者把自己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理解成“当代太史公”与新桥乡亲下广东奋斗史的关系。这个想法令我感动,也勾起我表达的愿望。
从《下广东》人物关系的设置,可以看出作者用心布局了一张很大的人物关系网。故事里的重要人物多具有较高程度的类型性或隐喻性,刻上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思考与认知。例如那位未出场就已经牺牲却又无处不在的黄仰岩,他无疑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走过的历史道路的缩影。从他那里出发,母亲与蒋中发这一对冤家的爱恨情仇,怎么看都有当代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价值取向不同的影子。他们毕生的隔阂和纠缠虽然结局有蒋中发在黄仰岩墓前的独白而暗示象征性的和解,但读者很清楚,那是小说而不是真实的生活。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三角关系牛爱、沙某和水娇,很明显地交织着当下改革开放中的人生困惑:如果财富与德性本来就不是天生的一对,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下广东”不仅没有消弭自古以来鱼与熊掌的冲突,而是把它放得更大。因为社会急剧变迁而把每一个人都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墙角,由此显露原形。那位原本美丽和淳朴的水兰,她的命运毫无疑问意味着与繁华和财富相伴生的阴暗和血泪,而无声无息几乎被人遗忘而独自躬耕的矮子为劳,则是那个日渐萎缩、破败的乡村传统的承载人物。我不清楚作者是不是非常有意识地这样去布局和设置人物以及他们的关系,作者的经历或许无意中提供了这样做的便利。从福建长汀下广东,由新桥到珠三角,空间的错位并没有妨碍它反映同一个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迁的落差,反而恰到好处地提供了文学表现所需要的集中性。不过无论如何机缘巧合,我也不相信一个对生活不上心,缺乏感受和思考的作者,能够如此自觉地将急剧变迁中的社会冲突、对峙和困惑精巧地编织进故事人物的关系网络之中。作者期待自己做这个时代社会的“太史公”,这肯定不是“无厘头”,而是“处心积虑”,至少是用心良苦。这是值得大大肯定的。对于有雄心写出至今难以有服众“说法”的当代史,或写活几个人物显露出这部当代史真相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嘉许的开端。没有能够承载复杂社会内涵的人物以及他们活动的关系网,要写好时代和社会,这无疑是空想。
然而,构思出这样有时代内涵的人物以及设置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是一方面,能够将他们尽可能完美地呈现出来是另一方面。这“另一方面”我觉得更能触及到小说更为根本的地方,故想就此谈一些看法。不过我毕竟没有写小说的才华,只是阅读比较多,在这样写好还是那样写好的问题上能提供一点儿看法而已。
就我所说的后半截,即尽可能完美呈现有时代内涵的人物以及写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言,我觉得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是作者需要对笔下的世界有一个完整的判断,能从纷繁杂乱的各种价值之中形成独有的发现。第二是作家要明白,小说反映社会反映生活是个批评的概念,而写好人物写活人物才是作家的看家本领,作家当以看家本领优先。因为读者对故事社会内涵的发现是通过所写人物及其关系而感知到的,越鲜活的人物越有助于读者感知故事的社会内涵。如果反映社会和反映生活的主观愿望优先而压倒写活人物,则小说的社会内涵就是干涸的、枯萎的,其美学趣味就要大打折扣。作者完整的判断和写活人物优先这两点其实也是彼此关联的。作家对笔下世界的判断越完整越鲜明,就越有利于写活人物;如果作家对笔下的世界认识越趋于时流,或者越混乱,则人物就越容易概念化,故事越容易成为传声筒。《下广东》在这两点上都是我深感惋惜的,作者已经“登堂”,却让自己止步在“入室”的门外。且让我多铺陈几句,把话说清楚。
长篇小说无论中外都源自各自悠久的讲故事的传统,它们或寄身于史诗、浪漫传奇,或寄身于章回、演义。长久的文学传统成为惯例,形成它们追求的美学标准。这个美学标准我觉得可以用“好看”来概括。但凡“好看”的长篇,情节完整而跌宕、叙述安排精妙而语言趣味盎然,它们都有极大助益使长篇故事变得“好看”。这悠久的美学标准在现代长篇出现之后并没有被抛弃,它只是沉淀下来,逐渐减退了它在美学诸标准中的绝对重要性而已。事情最初的变化可以追溯到现代长篇小说的开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出现。在这部小说里,虚构故事隐藏着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解释。虽然塞万提斯将自己的意图隐蔽得很深,但这绝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构成了现代长篇小说的亮色。是不是由于这个变化形成了现代小说“严肃”与“通俗”的分野,我不敢断定。但是如何解释人所遭遇的生活世界,这绝对是有志于写长篇小说的作者需要面对的头等重要的事情。当然作者可以回避如何解释生活世界的问题。一如既往追求“好看”,也是可以的,但写出来的作品多半会被归入“通俗”类。现代小说之所以为现代小说,即在于作家将解释生活世界的独特眼光灌注在故事里面,现代小说也因此而成为探索和发现生活真相的一种文学样式。都说好的现代小说与哲学比邻,包含另类的哲理,即由于此种演变的逐渐累积而成。
不过应当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作家对生活世界的解释看成与社会通行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科学观念对社会的理解完全等同的东西。如果完全一样,那作家就是在用别人的眼光来解释自己笔下的世界了。作家对生活世界的发现是独特的,这种发现给予读者的启发和它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成就。胡风当年批评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提倡作家应该有“主观战斗精神”,就是反对作家用一般的政治理念代替自己对生活世界的发现。作家对生活世界的思考和发现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它像生活一样是无穷无尽的。除非人类的生活形态到头了,不再有生命力了,那文学对生活的发现和解释也就止步在那里了。人们常常把文学中的教条主义看成是政治力对作家的规劝、强制,其实我更愿意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作者探索生活的意愿不足和思考力的退化。当你没有自己“手眼”的时候,借用别人的“手眼”,这是很方便的,同时也是懒惰的做法。借来的“手眼”显然就不能说是文学的探索了,不是吗?
从文学的事实看,作家对生活世界的解释不仅可以各不相同,你有你的眼光,我有我的眼光,甚至可以是“政治不正确”的。我们都知道《飘》的文化立场是反历史的。作者米切尔站在了南北战争的历史解释的对立面,但这并不妨碍《飘》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品。我们熟悉鲁迅的《孔乙己》。科举制度对孔乙己伤害极大,不仅夺去了他本该有的财富、健康,甚至夺去了他的灵魂,使孔乙己变成一具人世间行走的躯壳。鲁迅透过这个人物对生活世界的发现是振聋发聩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说法”,这不但偏颇而且不得要领。然而如果认为鲁迅对这一生活真相的发现违反了历史事实,偏激而愤青,这又是离文学太远,显出方巾气和酸腐味十足。文学对生活世界的解释与通行的意识形态观念、社会科学的知识虽然有联系,但本质上却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文学写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而人是高度复杂的。但每个社会通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它们是把人以及人的存在综合成忽略其个别性而成为一般要素,再加以提炼和表达的。若以后者为基础来写人,以后者来代替作家的思考和发现,依然是文学,但这种文学却不会感人。
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对这一点有非常强烈的自觉,他在自传性小说《抵达之谜》里讲述了他如何寻找自己对殖民地生活世界发现的过程。他是印度移民的第三代,自小生活在加勒比小国特立尼达。随着移民和世代变迁,本身的印度文化在殖民的土地上被稀释得不足以作为自身文化认同的内核,而因自身备受排斥,对殖民者的文化又格格不入。作为一个自小立志文学创作的人,何取何舍?他必须面对。道路似乎只有一条,就是认同殖民者的文化立场,模仿他们,追随他们,以殖民者的眼光为眼光,而殖民地的教育正是这样由殖民者灌输给像他一样的被殖民者的。换言之,这模仿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他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他说:“这些思想基本上是在英国富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为了成为那种作家(就像我解释的那样),我只能变得虚伪起来,我只能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假装自己是另外一种背景下长大的人。在作家身份的掩盖下,隐藏印度侨民血统的做法,无论对我的素材还是我本人都带来很大的损害。”[1]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假装自己是另外一种人,在中文世界里这种人早有名字,鲁迅早就写过了,叫“假洋鬼子”。奈保尔既不愿做“假洋鬼子”,又做不成完整的印度人,这个文化认同问题具体落实到写作就是写什么和如何处理笔下素材,如何确定主题的问题。作家通常要有自己的眼光,才能安排好素材的处理。他自己说,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才形成了一个作家必须有的对生活世界的解释,哪怕这种对生活世界的解释只是稳定的感触或者直觉。他说:我“终于明白了,我的主题既不是我的敏感性,也不是我内心的发展变化,而是我的内心世界以及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我的主题就是对我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作出的解释”。[2]他原来就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但却不懂得如何用自己应有的文学眼光解释这个生活世界,直到离开之后五年才琢磨出来。
他琢磨出来的观察和解释殖民地底层人生活的“眼光”最完美地表现在他的小说《米格尔街》里。他有十几本书被翻译成中文,《米格尔街》是他写得最好的。他写的是米格尔街的草根小人物,其原型来自于他童年至青年时期的家人、玩伴和熟人。奈保尔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的讲话里把这些殖民地移民小人物形容为“一无所有”的人。事实上,英国殖民者对土著和移民不算刻薄。五年劳工契约期满可以得到五英亩土地,并在那儿定居下来。若是较真,这“一无所有”也不符合事实。可是奈保尔特指的是精神上的“一无所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蕴含一种文学的眼光。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在本民族的文化被连根拔起的殖民地,土著和移民只能做殖民者强势文化可怜的“模仿者”。奈保尔独特的文学眼光正在于他发现了他的生活世界的这一真相。这个发现使他对自己笔下的世界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被殖民活动将自身文化撕裂得支离破碎的精神流浪汉的灵魂会有多么可悲可怜。他笔下的曼门,那个想成为受公众瞩目的大人物以至于行为乖张的人,他能想到会受大众瞩目的方法是参与政治。而他的参与就是在选举季节贴出大大的照片,照片下写着“投票”两字。在忍受了长期不受关注的沉默之苦之后,终于做出“壮举”,宣称自己是再度重临人世的耶稣,号召围观者、追随者往自己身上砸石头。还有那位自视自己是最伟大诗人的乞丐沃茲沃斯。稍为知道一点儿英国文学史的人,就知道这位乞丐连名字都是模仿得来的。他成为伟大诗人的方法是“每月只写一行”。写了五年,还要再写22年,“我就会写出一首震撼全人类的诗篇”。他的结局可想而知。我读奈保尔的这本小说读得不时发笑,又觉得世事辛酸,和读鲁迅《孔乙己》《祝福》那种感觉差不多。两位作家都幽默,而鲁迅写得比奈保尔沉痛。奈保尔写因殖民而产生文化上时空错位给弱势人物造成的悲剧,鲁迅则写同一社会古今变迁而给落伍者酿成的悲剧。
奈保尔笔下的殖民地社会几近一无是处。社会不公、生活贫困、无秩序、草根人物精神涣散而无所归属,他对殖民的批判是深刻的。然而,如果从历史或社会科学的眼光认识自15世纪欧洲人海外冒险以来的殖民活动,则又比奈保尔的眼光复杂很多。至少殖民活动给受波及的地方带来了更为进步的科学、生产力和对人类生活更有解释优势的文化观念。从长远的观点看,殖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演变,也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奈保尔从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的特立尼达成长为一个在英语世界乃至全球都广有影响力的作家,这一事实也说明殖民带来的并不全是负面的。我不厌其烦地将作家解释生活世界的眼光与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视点并置起来,无非是想说它们是可以不一样的。两者的联系虽然切不断,但却不是同一回事儿。在如何看待生活世界的问题上,作家是有“特权”的,可这“特权”不是什么人赋予的,或天生就有的。它是作家在漫长的岁月中感受、琢磨和思考中形成的。不懂得行使这“特权”,没有自己看待生活的眼光,缺少对生活世界的发现,故事揭示生活的深度和感染力就要大打折扣。
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现在才兜回来,无非是想说清楚我读《下广东》比较强烈的感受:作者似乎未能琢磨出属于自己的关于生活世界的解释,眼光欠缺统一性,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叙述中显示出混乱。作者十分敏感地捕捉到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对峙点和矛盾,可并没有消化这种来自生活的直觉,更没有从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关于社会变迁的眼光。不是说作者毫无这方面的眼光,而是在我看来,凝结在小说里的作者的眼光必须是统一的和完整的,而我从小说的人物和命运中深深感受到作家眼光的混乱和破碎,这是美学趣味上一个很大的弱点。我没有迁徙弄潮的经历,但也生活在同样的社会时空。若是要问我,作家应有的解释生活世界的眼光究竟是什么,可否直接告知?我无法作答。因为作家对生活的发现不是理念形态的,而是文学形态的,它们连带着直觉和感受,或者说它是直觉、感受加上才华的产物。我不是作家,如果能够直接明示出来,我就直接写小说了,不会在这里批评。谁不想用自己笔下的人物去表现这一巨变的时代呢?这是批评的极限。读者只能说出不满意的地方,却不能指手画脚来教训作者该怎么写。批评不能越俎代庖。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可是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却是人言人殊的。古人常用物是人非形容世道沧桑,可是谈到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却似乎应该颠倒词序,写作“物非人是”。人还是那些人,几乎就用一代人的时间,这个社会就从农业社会跨越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迈入城市社会。这不是“物非人是”吗?环境、生活方式乃至价值准则,几乎面目全非,可还是那一代人。欧洲国家几百年的路,中国几十年就跨过去了。我自小生活在青山绿水的东莞县,如今那里几乎全是厂房、住宅和道路,看不到农田。直至导航技术成熟之前,我不是如古人那样“近乡情更怯”,而是“望乡情已怯”,因为无法辨认回乡的路而怯于返乡拜访父老乡亲,几乎每次都迷路,最后停车路边等待朋友前来带路。说出来像是天方夜谭,可那正使我产生“物非人是”的感受。
我相信类似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感觉还可以用其他语言来表达,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它们意味着什么?一提到这种更深一层的理解,就来到了分歧或混乱的三岔口。作为事实存在,分歧和混乱也许就是常态,可是小说故事却不能一如事实存在那样分歧和混乱。如果那样,小说对生活世界还有什么发现呢?还会给读者带来什么对于生活的理解呢?作者笔下的母亲和蒋中发本来是一对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们的爱恨情仇是可以铺陈出深广社会内涵故事的,可是却被置于一个绝对的道德评判之下。蒋中发有什么风吹草动传到母亲那里,她都是那一声断喝“你给我跪下”。要说这没有一点儿喜剧和谐谑气氛,那也不符合事实。但是那一声断喝,如果在40年前还传递出若干高昂斗志的话,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未免不带上外强中干的味道了。而这正是她作为一个人的可怜所在。作者将她作为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所以没有将这种时代变迁带给人物的反讽传递出来。德里达晚年满怀激情阐述曾在欧洲大地徘徊的那个“幽灵”。在我的想象里,她就是一位这样“幽灵”似的人物。可反讽的是作者把她写成了现实世界里的人物,这样她便不可能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然而书中的故事却传递不出这一点。她的断喝令我想起18世纪乾隆八十大寿发生的事情。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来叩门贺寿,见面的礼仪必须有下跪环节。乾隆也是这一声“断喝”,和作者笔下人物的断喝,异代而同心。然而这一声“断喝”造成了外交僵局,这一僵局直接成为约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耻辱的导火线。道德的高地是容易找到的,但历史和现实却像迷一样令人绕不过去。对待蒋中发这个人也是一样,作者用一种省力的笔法去写,没有深入到人物内心的复杂性,把他当成一个赶上时代潮流的新乡贤人物,这当然不是全无道理。问题是回避了他身上与资本相连的特征,于是他同样成为了新时代人物的符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比母亲形象丰满一点,这主要存在于他生命史的早期部分,至于后来“弄潮”而发达的部分,则依然干瘪苍白。也许作者也感受到这个人物带来的困惑: 他对生活前景的超前预判、他卓越的营生管理能力和他对乡亲的热情,如果把这一切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罪恶”联系起来,会不会伤害到这个人物的形象?会不会贬低他存在的意义?会不会“黑了”社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作者切断了这两者的联系,他就只能是一个符号。在小说里母亲和蒋中发都是只有轮廓的人物,而《下广东》这个题目所暗示的宏大主题和题材而言,这两位都不应该只是轮廓性的人物,应该浓墨重彩去写。可惜作者化不开笔,我把这一切归结为作者未能做到对生活世界的发现,欠缺自己解释生活世界的独特眼光。
至于小说里写得最多的牛爱、沙某——他名字的谐音让人非常不舒服,恕我用某字替代,顺便说,这是美学上的失败,它是不可接受的——和水娇三人的爱恨纠缠,也和上文所说的弱点有关。既然要让蒋中发保持新乡贤人物的体面,新桥人浩荡“下广东”的发财史的阴暗部分似乎就不便与他相连。然而回避了这一点,作者应该知道连常识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把与“资本的罪恶”相连的“题中应有之义”集中放在了牛爱身上。他下广东大展宏图,靠的是新时代的“两手”——吹牛和蒙骗。硬到无坚不摧的这“两手”几乎天下通吃。他也从山村的穷教书匠变身为“中国民办教育的拿破仑”。在发财的时代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当然有他的喜剧性,他与马克•吐温笔下那些为了发财而疯癫了的人物也有相通之处。然而马克•吐温的基本风格是嬉笑挖苦,而作者的基本构思近乎“正面强攻”,所以光有戏剧性是不够的。但牛爱作为一个本质上不是喜剧人物的性格,仅仅在笔法上与喜剧沾边,就显得单薄了。他从山乡教师到下广东蹚教育市场的浑水,霎时财色兼收,他的蜕变史应该包括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这种内心的挣扎与痛苦甚至伴随着他发财史的始终。可作者只把他当成可笑的人物,尽情嘲笑一番。这算是美学的懒惰吧。这懒惰里面也透露出作者对生活世界的发现还是不够的。牛爱的结局近乎鸡飞蛋打,我猜是想让这个结局显示出古老的正义。用心当然是良苦的,可我觉得太廉价了。与其坏人有廉价的报应,孰如坏人在荣华富贵中备受良心的煎熬?当然如果牛爱能在财色双收中坐卧不宁,那就很难说他是纯粹的坏人了。总之,一个更具有多面性格的复杂人物更能够揭示生活世界的真相。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心》也是写社会急剧变迁时代伦理价值观冲突的。他与“正面强攻”的笔法不同,时代只是一个隐现的弱背景,但那个以牵强的理由安慰自己当年横刀夺爱的草根青年,在发达而成为老师的数十年后,良心的煎熬终于使他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他最后决定与当年自杀的朋友黄泉相会。这也算是故事对正义的呼唤吧,但怎么看都比牛爱大财得而复失又遭美人离弃的结局具有更深广的心理和伦理内涵。
看沙某的形象或者比较容易从德性坚持、做人独立不迁的正面去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写这个人物的初衷。围绕着他的故事我倒读出在这表层之下的深层心理的意义,这使我阅读的时候产生了意外之喜。沙某的个人命运与其说同牛爱对比显示出道德光辉的色彩,不如说折射了成长于无知封闭的年代的个人私生活备受挫折的悲苦。这是社会的问题,同时也是个人心理的问题。沙某有一个无比强势的母亲但却缺少父爱,从小被赋予苦读出人头地的重任,稍有不如母亲之意,即被那一声如雷吼的“你给我跪下”震慑到双膝发软,不由自主地下跪。俗话说,母强子弱。沙某的成长史精彩地演绎了这句有丰富心理内涵的俗话。母亲不但生他养他,更重要的是她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自然强势,使沙某实际上成为一个心理和人格不能健康发育的侏儒。虽然这个人格和心理的侏儒在职业的公众场合是以一个道德高尚的形象出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隐藏着人格发育的严重不足。这从他与水娇的关系中始终强烈地压抑本能,或者说始终不愿意用健康的方式接受水娇发出的异性信号中可以看得出来。童年至青年时期漫长的压抑,它催生了对异性的恐惧。这种恐惧继续腐蚀着他的心理和人格健全。长期的伤害最终以变态的方式爆发出来。他向陷于人生污秽之中的弱女子水兰公开下跪求婚,以此为道德的宣示和拯救弱者人生的法门。从文本有限度的显露看,作者对此虽有视之幼稚的微词,但大体上是肯定其道德价值的。因为沙某从此不再“虚伪”了,从此做回阳光下的自己。但我却认为,这种写法不无可议之处。我不排除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将怜悯当作爱情,但这肯定不是道德价值健全的表现。实际上这是人格和心理危机的爆发,从这个立意去处理素材,肯定使故事更加意味深长。因为自现代革命潮流席卷中国以来,性以及异性交往逐渐变成一个话题的禁忌,它无法出现在发育时期的青少年教育中,连文学表达也是避之则吉。这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的人格成长无可弥补的遗憾。沙某成长于这个时期的末端,而且有一个家庭地位简直如神一样的强势母亲,容易感染上社会封闭时期出现的“人格病”。当社会走上开放之后,感染了“人格病”的这一代人如梦初醒,为自己个人生活的无知、幼稚和混乱付出了代价。我阅读当代长篇小说有限,似乎还不曾见对这一主题有较深发掘的小说。《下广东》沙某的故事在这方面是意外的收获,它折射的是整整一代人在“性”这个问题上的悲苦,揭示了封闭兼高压教养下时代和人格的双重症状。我的确觉得,小说文本关于沙某的故事是一个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好文本,作者提供了一个好的案例。不过故事的结尾让他抱得美人归,这与写牛爱鸡飞蛋打的本意是一样的,好人最终也有好报,可惜就是有点廉价了。
我也在想,作者笔下重要的人物为什么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性格命运的不完整、欠缺内部一致性的毛病,其原因何在?我认为,这和对人物的熟悉、对生活的观察是没有关系的,相反对人物的观察显示出这是作者的强项,他与乡亲交朋友,非常熟悉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沧桑变故。如果剔除了下文谈到的修辞的弱点,小说里不少细节,生活气息还是很浓厚的。可是一个有生活积累的作者还要明白一点,一部长篇的构思应该围绕着人物及其命运来进行而不是围绕着反映时代和社会来进行。作者也许摆错了写人物和写时代的先后次序了,把时代变迁、新桥人下广东的奋斗史摆在了构思小说故事的第一位,把人物及其命运摆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写人物从属于写奋斗史。这也许是造成了上述缺陷的原因。这一构思缺陷体现在作者要做新时代“太史公”的美好愿望里,也体现在人物的出现不循性格的逻辑而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上面。例如小说写到三分之二,之前一直没有提到矮子为劳,没有铺垫,没有伏笔,突然让沙某困顿中想起他,接着拜访见面,两人长篇对话。对情节发展而言,矮子为劳的写法像天外来客。作者大概认为,缺少了这个人,就像舞台缺少了一个不能缺少的角色,于是添上去,一台戏就完整了,就像社会有各种人,给它配齐了,各方面代表角色就出场完毕了。这种构思的出发点就是时代社会优先,它造成了人物遮蔽。我不认为写人物还是写时代在小说里是绝对矛盾的,但作者的出发点确实有一个先后的问题。文学通过写活生生的人而显现出时代社会和生活的面相。这和历史不一样。就算是司马迁也只有在笔法修辞的意义上才是文学家,《史记》的篇目编排、大的构思是从属于探究历代治乱兴亡而“穷究天人”的。这显然不是文学的。文学以人始,以人终。所以小说的构思要以人物及其命运为出发点,只有在人物的性格命运里参虑到一致的完整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参透,才能最终在叙述中把人物与故事聚拢在一起。这也就是上文所讲的对生活世界的发现。马克思有句名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放在经济学、社会学思维里没有一点儿问题,放在文学里却应该倒过来理解:一切社会关系投射在人和他的命运里。社会关系不是抽象的,它要在人物的性格命运里,在人物的悲欢离合里。这样的社会关系才是文学要求的社会关系,否则就是有名有姓的抽象符号。
作者对生活世界的发现,对写人物还是表现时代社会的理解存在的落差,导致了故事讲述产生其他问题。比如人物对话冗长繁复,它们与情节推进脱节;故事只有背景气氛的近似而欠缺内部的情节统一性。这些恕我不展开了,否则就没完没了。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下广东》的语言风格。小说的语言风格,真是用得上瑕瑜互见这个词。作者对民间俗语、俚词、小调的运用,时见精彩。本为闽人,粤语词也用得很好,为故事讲述增添浓郁的乡土色彩。这种活泼生动的语言运用,说明了作者贴近乡土,善于观察的长处。然而小说中语言风格另一面却是冗赘之笔太多,叙述臃肿,形容过度。用王国维的话说,一个字,就是“隔”。叙述语言非但不能使读者进入要表达的“意”,相反却造成层层阻隔。言词的大山阻挡了阅读的行者。冗赘之笔集中表现在太喜欢使用成语。也许作者认为这样表达更加风趣,可以尽情挖苦,与无厘头的美学趣味相互配合。比如小说第十二章的句子,“新粤商会的牛会长新官上任,春风得意,乘兴出击,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小试牛刀,便让那帮农民大亨在一愣一愣之下,三下五除二,把一切都搞定了,让沙碧先前的万千烦恼,顷刻雪消,真的是停停当当,功德圆满。”这是糟糕透顶的句子,不知作者意识到没有。要是能用一个细节表现牛爱的本领与狡猾,这人物就有立体感了,何不胜过这隔靴的表达呢?像鲁迅写孔乙己“穿着长衫站着喝酒”,就这一句,胜过千言万语。语言既是能表达意图的工具,也是能遮蔽所表达的高墙。作者让自己的句子变成了脱离表达意图的话语,它就变成不知何所指的语词链条。在词的所指和能指之中,所指永远是第一位的。脱离了所指,能指无非就是语词的碎片,毫无意义。让我举十五章的一句做例子,“从还在老牛拉破车的闽西红土地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高歌猛进的岭南金三角”。如果将它改写成,“从闽西红土地突围出来,辗转到了岭南”,两句试比较,是不是删去了现成词语的后一句更加直截了当?再如“结局”的开头,作者写道:“烈日当头,黄尘弥漫,105国道上铁流滚滚,道路两边日新月异、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城市,甚至整个岭南大地都在摇撼和战栗。”夸张当然是必要的修辞,但这么高频率使用成语,这种夸张反而令作者要表达的真义更远,令读者生厌。冗赘的句子简直就是骈指,不仅多余,而且有害,严重影响文本的美观。不管场合合适不合适,句子充斥成语,过度膨胀的句子在文本里随处可见。我不清楚作者为什么这么喜欢使用成语,是不是职业偏好带来的?如果是,那便需要三思,因为它对文本的美感是有杀伤力的。
我也知道,写作说容易也容易,拿起笔就可以写,正所谓无中生有。可说难也难,让笔下的句子并句相连,产生感动人的共鸣,这委实是件非付出惊人努力而不可的难事。作者当有笑骂由人的淡定,走自己的路。而我作为读者写下上面的话,无非是想对作者今后的创作有所帮助。有道理就吸收,没有道理的弃之可也。
(写于2017年春)
[1] [英]奈保尔:《抵达之谜》,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2] [英]奈保尔:《抵达之谜》,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作者:林岗 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4期(总第31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胡一峰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