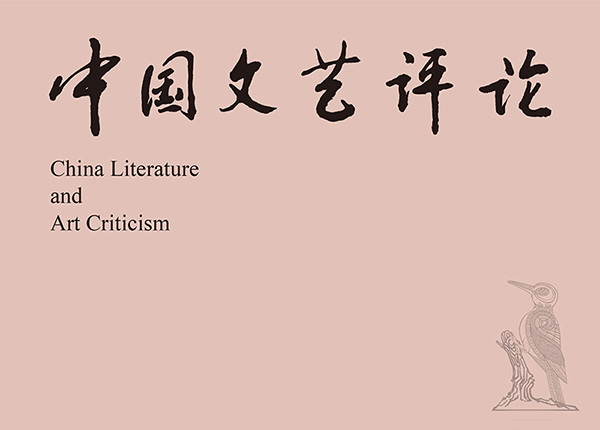
孙惠柱先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较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探索跨文化戏剧的学者和剧作家、导演。三十多年来,他在国内外不断进行形式多样的跨越类戏剧实践,著有《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社会表演学》等,剧作有《中国梦》《挂在墙上的老B》《白马Café》《宴席》,以及越剧《心比天高》《忠言》、京剧《王者俄狄》《朱丽小姐》等。作为一个跨文化戏剧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他在中西不同戏剧传统及文化的碰撞中,积累了自成体系的戏剧跨越的观念。
一、海外求学教学与“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
陈戎女(以下简称“陈”):孙老师,我看过您的《谁的蝴蝶夫人》《社会表演学》《心比天高》《第四堵墙》等书,这里有您对中外戏剧的研究,也有一些跨文化戏剧文本。我还看过您编的戏《王者俄狄》和《心比天高》,对您的戏和研究都很感兴趣。您是在国外完成的戏剧教育,而且很早就提出了跨文化戏剧的概念。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孙惠柱(以下简称“孙”):我1981年拿到上海戏剧学院的硕士学位,论文13万字,出书时叫《话剧结构新探》;10年后台湾再版时加了几万字,更名为《戏剧的结构:叙事性结构与剧场性结构》;二十多年后再次扩写为《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起初我主要研究西方戏剧,特别是结构形态和编剧法。我也写了三大戏剧体系比较的文章,但当时并不知道有“跨文化戏剧”(intercultural theater)的说法。
1984年出国留学,先学导演,本打算读完博士就回国,没想到待了15年。到美国后发现编剧和导演都不能读博,博士方向都是历史和理论。所以我第一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读完硕士,转学去纽约,先去了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因为纽约五所大学可以跨校选课,我还选了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课,1986年转到纽约大学正式成为他的学生。
什么时候看到“跨文化戏剧”这个词已记不清了,住在纽约自然会留意到跨文化戏剧现象,例如中国、日本的一些手段,也有非洲等地的一些形式。但最早的美国戏剧常涉及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关系,这是内容的跨文化,还有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故事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喜欢讲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纽约有个泛亚剧团(Pan-Asian Repertory Theatre),我曾给他们做过顾问,他们也找我导演了我的一个戏。1989年我离开纽约,先后在四所大学教授戏剧文学、戏剧史、编剧和表演,也开始导演。
1992年,谢克纳邀我参加他组织的“跨文化表演”(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研讨会。会上我第一次提出“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thematic intercultural theatre),我认为跨文化戏剧应该从戏剧史的源头算起,如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而并不是西方学者说的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他们最多也不过推到世纪初。在我之前好像没人这么看跨文化戏剧。萨义德的成名作《东方主义》也提到戏剧,但他不说跨文化,而是把相关剧作称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t)作品,全是批评:《波斯人》宣告东方是被打败的,《酒神的伴侣》又表明东方是危险的。很奇怪他没提《美狄亚》,其实《美狄亚》知名度远超《酒神的伴侣》《波斯人》,因为女性主义兴起,《美狄亚》是1960年代后西方人演出最多的希腊悲剧。萨义德知道《美狄亚》广受好评,不便拿出来批评,所以故意不提。他对那两个希腊剧本只下一个简单的否定性结论,没做具体分析。我认为所谓“东方主义”的古希腊戏剧就是跨文化戏剧,因为希腊人写出了文化他者的形象。这次会议后,我开始将“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付诸笔端,写了些论文,1999年回国后申请到国家社科项目,写了《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那时候国人还不太知道跨文化戏剧,少数关注者也只注意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
陈:为什么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多,而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少呢?
孙:在美国内容上跨文化的戏剧较难演出。20世纪60年代起大家接受了多元文化主义,容易拿到资助的是把文化分隔清楚的剧团,如亚裔、非洲裔、拉丁裔剧团。他们强调多元文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文化自信,问题是你的声音能和别人的声音分开吗?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分不开,而那些单一族裔的剧团又没法演反映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矛盾的戏。此外,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警告白人别再歪曲文化他者,吓得那些“政治正确”的人都收手了。相比之下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就容易多了。
我的兴趣更多在内容上的跨文化。我曾在美国戏剧研究学会的年会上组织一个论文组,征集到一批很有价值的论文,换个角度去看熟悉的戏剧史。如有一篇论文研究《威尼斯商人》在以色列的演出史,有人说这部剧反犹,不可以演出,也有人说可以演。一出戏牵涉到跨文化冲突,总会有人反对,完全四平八稳就不好看了。当时做跨文化戏剧,涉及到黑人和犹太人都还有些禁忌。我在美国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是个犹太人,但研究黑人戏剧,我提醒他说黑人可能会不接受。他说不怕,因为20世纪60年代他参加过民权运动,和黑人一起坐过牢,有了黑人研究的“通行证”。他研究的美国minstrel show(黑人滑稽剧)也是跨文化戏剧,最早白人涂黑了脸“丑化”黑人,后来被美国人视之为种族主义的耻辱。这种戏剧也有发展,黑人演员逐渐取代了白人,但在表演时却又向以前“歪曲黑人”的白人演员学了很多东西。其实黑人的自我嘲讽也很厉害,比如nigger(黑鬼)别人不能说,他们自己就可以互相说。所以这位学生研究的黑人戏剧和形式、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都有关系,揭示出黑人戏剧中一些深层的含义。
我指导的第三个博士生是美籍华人,现在是加州大学教授、美国戏剧研究学会主席。美国有两个全国性戏剧学会,ATHE (American Theatre in Higher Education美国戏剧高教学会)的年会有一两千人参加。ASTR(American Society for Theatre Research美国戏剧研究学会)专注学术研究,年会大约有200人。我曾在一个会上发表过论文《当中国将军遇到他的“蝴蝶夫人”》,探讨杨四郎等人的跨文化故事,但后来没再继续,我的博士生就用这题目写了论文。她发现苏武等人其实多在番邦结婚生子,并不是传说的那样孤苦伶仃与羊为伴。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讲汉族和番邦关系的戏,很像《蝴蝶夫人》:强势文化的男性和弱势文化的女性走到一起,男人一听到祖国召唤就抛弃弱势的女性走了。她还比较了王昭君的历史和舞台形象,历史上王昭君在匈奴结婚生子,戏曲里她却在界河投河自尽了;是汉族文人不让她嫁过去受“玷污”,用笔把王昭君杀了。
现在我有个博士生正在写《四郎探母》。我发现《四郎探母》可能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适合给外国人看的好戏,成就超过《蝴蝶夫人》《西贡小姐》。那几部西方戏都有大男子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也就是萨义德批判的东方主义问题。慈禧太后很喜欢《四郎探母》,她对萧太后和佘太君的身份都认同,因为满人已征服汉族,又大量接受了汉族文化,所以心理相当平衡。一般人在创作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时很难做到完全的平衡,但《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与铁镜公主、佘太君与萧太后,无论戏份多少还是作者的态度都平衡到不可思议,举世罕见。《四郎探母》曾在各地被禁无数次,但后来都开禁了;该剧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味,在文化交流和文明冲突都日益凸显的当今世界上具有极大的意义。
陈:我们知道,您在海外求学时受到您的老师谢克纳的影响,他是海内外知名的“环境戏剧”和“人类表演学”的倡导者,身体力行,能否谈一谈您与他的交往,以及您受到的影响?
孙:现在不少人热衷于“沉浸式戏剧”,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我出国前写了一部戏《挂在墙上的老B》,用戏中戏的形式,演员每演一段,导演问观众怎么样,逼观众参与;但戏又是有秩序的,演出过程中不可以随便上人。这在1980年代算是很先锋的。但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写中国1930年代熊佛西领导的农民戏剧实验,就发现这些农民戏剧实验有非常高的观众参与度,那时不叫沉浸式,就是观众参与。谢克纳的《环境戏剧》讲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戏,他对我这研究很有兴趣——原来中国那么早就有了观众参与的实验戏剧。我发现熊佛西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时,并没想推西方人的环境戏剧——那时也还没这概念,他无意中发现,农民看秧歌习惯和演员打成一片,他就把这个观剧习惯用到了话剧中去。谢克纳一辈子都是先锋派,几乎不去百老汇,对主流戏剧不感兴趣。而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主流戏剧,要靠有好的剧情人物、能吸引观众的戏来提高主流戏剧的总量,不应盲目鼓吹先锋派(它在美国也只是主流戏剧的补充),尤其不应在还没有主流戏剧、老百姓都看不到戏的情况下盲目推崇先锋派、新花样。
谢克纳是我的恩师兼挚友,但我对他也不只是一味恭敬,我在中英文写作中都明确表达了与他不同的观点。谢克纳本人也有一点回归经典的转变。2005年上海戏剧学院(简称:上戏)成立谢克纳人类表演中心,他2007年在上戏导演的《哈姆雷特》,与他的成名作《69年的狄奥尼索斯》有很大不同。早期他常把经典切割得支离破碎再彻底重构,而《哈姆雷特》就基本保持了原剧的完整。但我还是在一件事上跟他产生了严重分歧,他说中国有很多方言,戏里也应有三种,宫廷说普通话,哈姆雷特和同学说上海话,奥菲利亚和父亲、哥哥则说广东话。我发现这样做问题很大,中国话剧要求标准普通话,哪怕上海籍演员在台上讲上海话都会忍不住笑场,其他演员还听不懂;其次,剧中用方言一般都是为了喜剧效果,而《哈姆雷特》并没那么多需要喜剧效果的地方。我跟谢克纳表达了我的观点,起初他并不同意,之后他让全体演员开会发表意见,发现用方言确实无法交流,他立刻决定妥协,只用了几个词的方言。
陈:除了您不再倾向于先锋戏剧,您与谢克纳还有其他观念的不同吗?我注意到谢克纳提倡的是人类表演学,但是您的一本书名为《社会表演学》,如何理解这二者的不同?
孙:我写过文章讨论谢克纳的人类表演学和社会表演学的异同,强调了不同点。我认为社会表演学是人类表演学的中国学派,其基本矛盾是规范与自由。西方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左派,而谢克纳又是世界著名的先锋派导演兼思想家,当然是偏向自由的,其理论往往强调打破规范——尽管他的表演训练和编辑实践都有很严谨的规范。我回国后发现我们两方面的问题都有,外国人总认为中国自由不够,其实我们规范方面的问题也很大,很多地方我们的自由比美国都多。人类表演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鼓励人人做完全自由的选择。事实上,从萨特到当今左派学者都忘了自己从小学的很多规范已然成为下意识的第二天性,他们做选择的时候对那些规范是不会打破的。但西方人总喜欢告诫我们,中国需要的就是自由,很多中国人也真信了,什么事都要自由,无视规则意识的问题。鉴于中国的情况,我认为自由当然需要,但也绝不能忘了规范,当下的中国很多行业都缺乏规范,就是想守规范的人,也不知道规范是什么。
所以社会表演学跟人类表演学有哲学基础的不同。社会表演学的哲学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一定要跟其他人生活在一起,不可能独自存在。有人爱说只要不害别人,就可以一切都按自己的欲求来做,事实上完全随心所欲的人一定会伤害到别人,所以“社会关系”一定有规范。社会表演学的哲学基础还有儒家,“礼”的学说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表演学,被五四运动废了,百年来很多社会规范一直没有重新立起来。我常常问学生:“当你离开父母一段时间,回家见到父母的一刹那有什么肢体动作?”少数人说拥抱,这是学的外国礼仪,影视上看来的,但多数人还不习惯,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好用接过行李来化解尴尬。我一个博士生称之为“三秒钟尴尬”,因为不知道相见时该做什么,磕头、握手都不好。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实在应当从最基本的“长幼相见礼”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礼仪规范,不能只破不立。鲁迅1919年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当时西方流行的生物学、进化论,甚至还有“善种学(Eugenics)”——就是现在已被普遍否定的优生学。他的倡议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和现在常听到的西方说法一样。“尽力的教育”和“完全的解放”是很好听,问题是可能兼容吗?教育者一定要教学生规范,让学生“完全”解放就不用“教”了。我们长期以来被这些好听的口号所误导,要么教育的规范极其死板,要么一解放就放弃规范,不能适应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变的情况,找不到规范与自由之间合适的度——这就是社会表演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我回国后头10年主要讲社会表演学,学生的论文也多与此相关。这些并不是谢克纳关注的,但他听说后很有兴趣,他非常开放,认为人类表演学(Performance Studies)在不同国家可以不一样。我刚回国时有人建议我全面翻译引进人类表演学,第一个引进者可以跑马圈地。但是我不想仅仅引进,而要根据国情的需要开展自己的研究。近年来我的观点又有发展,给“人类表演学”重新下了一个在中文语境中更易于理解的定义:包含“艺术表演学”和“社会表演学”两大分支的研究人类所有表演活动的交叉学科,艺术表演学的范式既有助于理解社会表演学,也可以用来进行社会表演的各类培训。所以我近年来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以戏剧为核心的艺术表演学上。
二、戏曲与西方戏剧的结合:《王者俄狄》等跨文化剧作
陈:我们谈一谈您的戏剧作品吧。我因为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关系,注意到您改编了希腊悲剧。您能说一说《王者俄狄》这个剧本面世的来龙去脉吗?
孙:美国导演、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Elizabeth Diamond(伊丽莎白•戴蒙德)来中国时被中国戏曲吸引了,想跟我合作,用戏曲做一个西方经典,我就想到了希腊戏剧。新世纪初我看中国电影《生死抉择》时,曾联想到俄狄浦斯的伟大。那电影讲一位高官的妻子接受了巨额贿赂,高官本人被蒙蔽了,最后他查明真相,把犯罪的妻子送上法庭。我当时想,大义灭亲还不算稀奇,真稀奇的是“大义灭己”,俄狄浦斯就是那样。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像俄狄浦斯这样一个在名誉上大义灭己的人。一般人印象中俄狄浦斯是个老人,但我将俄狄浦斯改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少年天子”。第二年,著名川剧演员田蔓莎与戴蒙德说好合作《王者俄狄》。2007年秋上戏办了一个国际戏剧节,她俩用工作坊的形式做了几个片段。后来戴蒙德没时间再来,我把戏给了上戏导演系主任卢昂,他找到浙江省京剧团团长翁国生,我们就开始了新的合作。2008年秋该剧在巴塞罗那首演,2009年上戏举办戏剧节,浙京又来上海演出此剧。
陈:这部剧我和同学们看过很多次,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喜爱。您能谈谈对这部戏的评价吗?
孙:《王者俄狄》和《心比天高》都是在杭州排的,剧本都经过导演改动。在我八部已经演过的戏曲中,这两部最早。那时候我自己对戏曲懂得还不太多,再加上剧院在杭州,我当时任上戏副院长,工作比较忙,排练不在现场,剧本就让他们去改了。我的改编与希腊剧本相比主要有两点改动,一是主题,俄狄成了理想主义的少年天子,二是结构,让全剧从俄狄主动出逃开始。《王者俄狄》演出中有些改动我觉得还不理想。索福克勒斯经典的剧本非常紧凑,一两个小时把很多年的经历都说出来了;我想更多地发挥戏曲特色,将前史用明场演出来,虽不必从出生开始,但俄狄十几岁自主出逃就要展现在舞台上。我的剧本是这样开始的,俄狄出逃后在路上撞见老王的马车。这场戏应当是打戏,2007年上戏排的片段就有这一段。但卢昂导演认为原话剧的结构更好、更紧凑,删除了前面的俄狄出逃,后来演出都是从俄狄当国王后遭到瘟疫、去见神算子开始。

《王者俄狄》剧照
陈:我从资料里看到,这出戏还有一个120分钟的版本,您看到过吗?
孙:曾经有一个近三小时的版本,翁国生让我加了丐帮的戏,因为京剧中有关于丐帮的程式,可以用进来。但我没看到演出。这一版过年时下乡演出过,农民认为俄狄弑父娶母的故事不吉利,差点踢台,所以这个版本再也不演了。常演的版本在75分钟左右。
陈:除了农村演出时出现意外,这出戏在国外演出时效果如何?
孙:《王者俄狄》2008年秋到巴塞罗那国际戏剧节演出,下午和晚上各一场。下午场因技术问题,演出没有字幕,只能让观众猜演员在说什么。演出后,新西兰国家戏剧学院院长安妮•鲁丝(Annie Ruth)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还出乎意料地掉泪了。她本想《王者俄狄》的故事很熟悉,又以为京剧只是技术上高明,但看到王后伊俄卡斯忒自杀时竟情不自禁地流了泪。这段戏在希腊原剧中并没有台词,但我们的改编让王后唱了一段。露丝导演说,虽然不知道演员唱了什么,但是可以想象唱的内容,她受表演的感染不禁流下了眼泪。当晚她又看了一遍演出,这次有字幕了,她忙着看字幕却没掉泪了。第二年2009年5月,她来上海开会又看第三遍,这次看字幕不用那么专注,所以还是掉了点眼泪。
字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常遇到一些外国人说字幕无所谓,因为艺术超越了语言,特别是西方经典,故事都知道。但编剧的每一句台词都是精心推敲过的,翻译也动了很多脑筋;外国观众未必知道编剧的改动、导演的阐释。如《心比天高》中海达烧书的动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不知道唱词,光看演员甩水袖,观众只能把自己的解释投射到演员身上——像露丝导演那样,这方面能力特别强的人可以少看甚至不看字幕,但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本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我这个观点,都用字幕了。

《王者俄狄》剧照
陈:《王者俄狄》的戏曲场景,感觉整个舞台非常的空灵,这是因为中国的舞台本来就是空的,还是受到了布鲁克《空的空间》的启发?
孙:戏曲的舞台本来就是空的,考虑到出国演出,也不能做复杂的布景。《空的空间》中的看法跟中国戏曲是很贴的,但戏曲不用受布鲁克的启发。
陈:《心比天高》和《王者俄狄》的戏曲语言,您觉得满意吗?
孙:总体上很好。不过,《王者俄狄》前面加了一大段画外音,像电影或话剧。我做《朱丽小姐》也遇到类似情况,不少戏曲艺术家都有加入话剧手法的冲动。他们到戏剧学院进修后会发现西方的东西比戏曲高明,常要加点西方元素进去,但我常跟他们相反。《朱丽小姐》排练中有些像话剧的手段就被我否决了。我认为戏曲的东西挺好,总要他们告诉我,还有些什么戏曲的技法可以用进去,可惜年轻人学过的传统技法还不够多。相比之下《心比天高》《朱丽小姐》的戏曲化更极致。
陈:《王者俄狄》的推陈出新中,观众普遍觉得神算子设计得特别好。
孙:是的。这个设计应该是受了1987年上海昆剧团《血手记》(《麦克白》)的启发,那里一开场有三个女巫,得到普遍的好评,所以就学过来了。剧本上有三个神算子,出国时有时候只用一个。
陈:看来,当代戏剧也涉及到戏曲老传统和新传统的传承。神算子的设计和道教有关系吗?
孙:神算子的服饰借鉴了道教的服饰,但在内容上无关,希腊故事里是神示,转译到中文语境就是算命。
陈:《心比天高》也是您和费春放老师回国后做的跨文化戏剧的重要代表作吗?
孙:是的。1999年我回国后,去北京语言大学参加易卜生国际会议“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会上有关于《海达•高布乐》的研讨,在西方人眼里《海达》是超越《玩偶之家》的,但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戏。会上挪威人听说中国人居然不知道《海达•高布乐》,感觉很奇怪。我就建议排一个戏曲版的《海达》。后来我和费春放开始写戏曲版的《海达•高布乐》,写成后又拖了很多年才演出。最开始是给上海沪剧院写的,上海的沪剧是个特殊的戏曲剧种,和话剧最接近。沪剧程式中几乎没有水袖,还有个别名“西装旗袍戏”,最适合演民国戏,如《雷雨》就是沪剧的保留剧目。海达是现代人,可以穿旗袍,所以用沪剧来演是合适的。后来一直没排,五年后我们把剧本给了杭州越剧院,导演是支涛(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主任)和展敏(杭越副院长)。沪剧剧本的字数超过现在越剧的两倍,沪剧更接近话剧,语言容量更大。《心比天高》改成越剧时,编剧在我和费春放之外还加了吕灵芝,她根据导演的要求删了原剧本很多字,现在这出越剧很难看到话剧痕迹。

上海戏剧学院京剧《朱丽小姐》在米兰皮克洛剧院演出海报
《心比天高》曾到挪、印、法、德、美等不少国家演出,因为演出成功,挪威方面要我们再做一个易卜生越剧。我们选了《海上夫人》——也是从未在中国上演过的。这个剧本写出来到上演没多少改动,从那以后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合作:先写提纲给导演看,导演提意见后,根据修改的提纲把剧本写出来,跟导演的配合更默契,彼此都学到很多东西。
陈:跨文化戏剧在剧本改编过程中的增加和删减如何定夺?
孙:西方戏剧经典改编成中国戏曲,一定有削减,因为戏曲要留出非常大的空间给歌舞,所以人物和情节都要简化。我们最初改编的几个剧人物都不太多,比如《朱丽小姐》本来就三个人;《海达•高布乐》把次要人物删去,只留五个;《海上夫人》也删去了好几个,保留六个人。删得最多的是根据《李尔王》改的《忠言》(杭州越剧院2016),人物砍掉一半,还有十几个;李尔身边的两个老人并成一个太医。戏曲必须突出重点,重点的人物和场面会放大,要用歌舞表现。
陈:《心比天高》和《王者俄狄》中的焚稿、自杀和自盲双目都用水袖来演出,这种表演方式是您的意见,还是导演的想法?
孙:《心比天高》中的焚稿用水袖来演,是一开始就想到的。我们知道《海达•高布乐》里有两场戏用戏曲可以演得比话剧好,就是焚稿和自杀。焚稿肯定要用水袖,但怎么用、用多长的水袖是导演定的。本来还没想到水袖必须是古装,《心比天高》的导演支涛和展敏在劝我们把“西装旗袍”改成古装时说,不穿古装就没有水袖,也就没了越剧的特色。这句话说服了我们,一看演出就知道,水袖对于整场演出太重要了。有趣的是,周妤俊和翁国生这两位演员认识,二人都说自己的水袖更长。这两部戏用的都是超长水袖,不是常规的,这个技巧很难。
陈:您现在是坚定的古装派吗?
孙:支涛、展敏把我变成坚定的古装派十几年了,但最近因为做《悲惨世界》又有所变化,对于外国经典要不要本土化,有些否定之否定。《悲惨世界》的改编版众多,有电影、音乐剧,10年前中国戏曲学院做过洋装版的京剧《悲惨世界》,但没能留下来。那小说和历史关系太紧密,好像很难本土化。我以前做的跨文化改编都是人物较少、背景较简单的,《王者俄狄》《心比天高》跟历史关系不大,有点像寓言,就可以本土化、穿古装。而我们做“韵剧”《悲惨世界》折子戏时用了洋装,各地的中小学生都非常喜欢。但我们最近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个专业提高版的大型音乐剧,又决定回到本土化的路子上,不过这次不是古装戏,只是年代戏,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的黄土高原上。
陈:您觉得跨文化戏剧的目标观众是哪些人?
孙:首先当然是中国观众。因为有些戏在外国首演,有人以为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如我最近的京剧《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国内还没演过,已在意大利演过两次;越剧《忠言》也是先去希腊戏剧节演,后来在广西参加了国际戏剧节。这是因为有些剧团拿到国际活动的邀请后更方便从政府申请相关资金补助,但我们心目中的受众首先是中国老百姓,特别是戏曲老观众,当然也要发展大学生新观众。我把戏曲和西方的经典结合起来的时候,绝不随意解构,就是要照顾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现在有不少导演喜欢东拼西凑,但我认为要保留戏曲的艺术形式的完整性,西方经典的故事和人物也最好保持完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就像我对俄狄浦斯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故事还是完整的。这些戏的演出及其接受说明,这是最好的结合方式,可以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看到完整的人物形象,以及京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的魅力。
陈:我们最近看了2015年由中国戏曲学院演出的《明月与子翰》视频,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晚出现的戏曲版古希腊悲剧了。您是编剧,能谈谈这出戏吗?
孙:这出戏的导演是我的博士生刘璐,第一次演出是2015年12月在中国戏曲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演出。2016年初还到上戏的冬季学院演出。
《明月与子翰》可算我最得意的改编,改到让人几乎认不出原作《安提戈涅》。多年前上戏一位老师带着京剧风格的《安提戈涅》片段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戏剧节,大获好评,回来后他请我改编全剧。我觉得《安提戈涅》有点说教,就站在那里讲道理。因为神话中戏还没开始两位王兄就都死了,全剧的冲突聚焦于“葬还是不葬”,这对于宗教观念不强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死板、古板。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把前史改为一个兄长生死未卜,冲突转化成“救还是不救”,这就揪心抓人了,而且突出了“关爱生命”这一最核心的现代观念。这样生死搏斗就有了更多的跌宕起伏,剧中人物也有了更大的活动天地,而这只有戏曲才能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三、跨文化戏剧中的改编与原创、先锋与传统
1. 跨越类戏剧:改编抑或原创?
陈:陈士争导演1996年的实验京剧《巴凯》,曾去希腊演过,在北京也演过。罗锦鳞先生不太认同《巴凯》这样以西化框架演出的跨越类戏剧。对比而言,《王者俄狄》采用中国戏曲的形式时没有肢解京剧。但是《巴凯》其实是一出希腊剧,京剧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在,而《王者俄狄》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出京剧,不是一出希腊剧,您觉得对吗?
孙:对。上戏宫宝荣教授有一个观点:改编经典的戏曲就跟原创一样,无论改编者持有哪种理念,都无意拘泥于忠实原著,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从事一种创作。我们把《心比天高》等剧定义为再创作reinventing。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未必需要了解经典原著;但要使外国人有兴趣,还是要告诉他们改编剧和西方经典的关系,否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看一个无关的中国戏。当他知道这个京剧《明月与子翰》原来是《安提戈涅》,《王者俄狄》是《俄狄浦斯王》,就会产生极大兴趣。
陈:我看的资料说,《巴凯》是美国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EH)资助,然后派了纽约希腊话剧团的艺术总监Peter Steadman(彼得•斯坦德曼,已去世)主导。一个做跨文化戏剧的德国评论家费舍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严厉地批评《巴凯》,她认为这个剧有很多美国的意识形态在里面,实际上就把中国的京剧肢解了。她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世界各地对希腊悲剧《巴凯》的跨文化搬演的得与失。
孙:我知道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对戏剧几乎完全不给钱,而德国、法国是有很多政府资助的。NEH只资助学者做研究,NEA(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国家艺术基金会)才资助一点艺术,相当于最小的文化部,曾经一年只有一亿美金。我在美国时听大家打趣说,连给国防部军乐队的钱都比这更多些。国防部应该有好几万个亿,而NEA只有一个亿。
陈:费舍尔-李希特比较警惕在跨文化戏剧中政治因素的渗透。
孙:西方人在西方语境中掌握了话语权,有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有些左派学者喜欢借用萨义德的说法,说东方人“不能代表他们自己”。萨义德是借了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话“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必须被人所代表”。但这只是因为西方学者不懂别人的语言,就以为非西方国家不能代表自己,事实上东方人每天都在代表自己,只不过你不懂而已。中国人不能代表自己,只能让汉学家来代表吗?在我们这里,中国人每天都在代表自己。
陈:我们学习希腊文学的学生有时难免有疑问,古希腊戏剧在他们看来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典、经典,是历经两千多年传下来的。如果我们用跨文化戏剧表现它们,势必要经过自己的改编和演绎,那该怎么保证改编与原典是一样的呢?
孙:不需要“保证”改编版与经典所要传达的东西一样。我们要表现的就是从经典中引申出来的新东西,如果改编后对现在的受众有益处,就会留下;如果没意义,就留不下来。至于原来的经典究竟怎么解释,很难定于一尊。事实上,罗念生先生翻译的剧本一般人也不太了解,改编如果不做大改,多半没人看。当然,若既懂原典又懂戏剧的戏剧顾问能给观众做个导赏,讲一讲两者的异同,那是最好了,可以帮助观众得到更多。
陈:台湾传奇剧场也做了大量的跨文化戏曲,您对他们的作品如何看待和评价?
孙:吴兴国的第一个戏《欲望城国》做得最好,他的《李尔在此》成了向外国人展示个人才艺的独角戏,老戏迷估计不太感兴趣。但传统戏曲形式的跨文化戏剧可以让多种文化的人共同受益。我个人不想间离掉一个老观众,要让老观众仍然喜欢看;但又要让他们看到新的内容,前提是在形式上和老戏的印象有交叉。当传统戏曲形式的跨文化戏剧让人听到音乐是熟悉的,看到人物也是古装的,老观众就愿意去听去看。如果就是一个人演几个、十几个陌生的人物,谁知道在演什么呢?“陌生化”到令观众感觉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的,如果我们做一个原创京剧给外国人看,对方产生不了一点联想,为什么要请他们看呢?
2. 戏剧语言:淡化抑或看重?
陈:您怎么看铃木忠志和他的作品?
孙:铃木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认识到传统能剧的价值,尽量把它融合到他的创作中去。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戏曲艺术的价值要比能剧大得多,能剧有宗教味道,不能随便改动,而戏曲更世俗,很灵活。我们应该尽量把戏曲的好东西用起来,不要老是迷恋话剧先锋派的手法。我现在对多数先锋派不感兴趣,我们常常“自我东方主义”。以前先锋戏剧都是白人的,那些大师在老家已然过气,现在中国人却请他们来拼命吹捧。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戏曲、曲艺,就应该从这之中吸取些可以用到现代戏剧创作中去的营养。
陈:您认为在戏剧的表演里,涉及到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时候,关注点还是应该放在戏剧本身是吗?
孙:没错,很多人花了很多钱来做表面上、形式上的跨越,但更重要也更困难的是内容上的跨越。德国的跨文化戏剧家中,布莱希特主要是形式上的跨文化,莱辛是内容上的跨越,如《智者纳旦》这样的戏。很多先锋派搞形式上的跨越时都运用语言的混杂,我不赞成。他们宣称语言不重要,贬低剧作家,这种说法出自阿尔托。而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戏中的语言混杂并不是导演想贬低剧作家,而是想用“我们用了不止说一种语言的演员”来体现跨文化性?我最近在国家大剧院看了铃木忠志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其中一个中国演员演国王彭透斯,说汉语,其他角色都是日本演员,讲日语,现场放中文字幕,而中国演员讲中文的时候没有字幕。这样的演出现象您怎么看?
孙:铃木忠志有一本书叫《文化就是身体》,贬低语言,把一切归于身体。戏剧可能只跳舞、只演哑剧吗?这种源于阿尔托的说法在西方大学确实流行。那里的戏剧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并非教授故意误导大家,而是因为他们要发表论文,必须追新逐异,回避人所共知的主潮,所以多数学者都是只占剧坛10%左右的先锋派的拥趸。这个学术研究求新不怕偏的现象对西方观众没什么大影响,因为普通人并不看教授写的先锋理论,就是戏剧人也很少看,他们知道占90%的主流是剧本戏剧,真要看的是主流报刊的剧评。但在非西方国家里,曾经跟那些先锋教授学习的海归很容易盲目地把先锋派捧成唯一。中国戏剧界的海归其实并不很多,但大量译介进来的书在崇肢体、反戏剧、后剧本。现在很难看到好的剧本,“文盲戏”倒很多——这是我发明的词,指不需要语言、只靠肢体、多媒体的戏。我们都知道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但是从阿尔托开始,包括铃木忠志也相信,文化就是身体,不需要学习语言,甚至还宣称剧本戏剧已死。这绝不是事实。
法国人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写了一本书《戏剧在美国的衰落:又如何在法国得以生存》,宣称美国戏剧衰落了,剧本戏剧干脆已死。这完全不是事实,却有很多人还当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听到西方来的类似惊人之语,而多数国人并不了解那里的戏剧教授的“套路”。20世纪前半期欧美还没什么戏剧系,介绍进来的外国戏剧作品都是好剧本,现在来看大多数剧本都还很优秀。那时欧美的戏剧研究大多出自文学系,1950年代起大学扩招,纷纷成立独立的戏剧系,为了创个性,就要和文学分庭抗礼,硬说导演最重要,贬低起关键作用的剧本。事实上戏剧文学可以历2500年而依然闪光,而一心打自己品牌的大导演常常没玩多久就自我间离出去了。像格洛托夫斯基是位了不起的大师,但更多是精神世界的而不是剧坛的大师,他在去世前好些年早就主动退出剧坛做隐士去了。
我近年来弄明白了戏剧界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只中国,甚至全世界非西方国家程度不等地都有这个问题。那里的戏剧大部分都由海归主导,中国大陆戏剧界海归还不多,但中国港台地区、日本、新加坡等地就很多。现代戏剧本源自西方,大家都去西方学,海归后自然就传播那些先锋教授的戏剧观念,而对英美法德意大利的戏剧总貌不甚了了。西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戏剧绝不是只占10%的“后剧本”先锋戏剧,但发论文的教授却有90%在鼓吹后者。大多数海归并不清楚,西方国家主流戏剧已经发达到饱和了,大城市每天几十上百个售票演出,多数大学戏剧系的教授和学生都很难挤进去,他们只好做边缘戏剧,不进剧场街头广场也可以表演。可在我们这里,根本还没有大众可以经常买廉价票观看的主流戏剧,也一窝蜂去做先锋派戏剧,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这个情况按说不应在中国发生,中国原来并不是没有戏剧的,但现在老百姓就是没有戏看。媒体说的“主流”是指宣传方面的主流思想,其戏剧跟大部分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要用“人均戏剧量”这个概念才更有意义,看看每个城市一年有多少正式演出,售票情况如何,除以人口数就有了——我们人口基数这么大,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不从受众的角度看,只满足于盖了多少剧场、抓了多少剧目、得了多少奖,对人民大众有什么意义?我们的人均戏剧投入不能算低,但实际让老百姓享受到的人均戏剧量太低了。
在人均戏剧量几乎世界垫底的情况下,不应鼓励大搞先锋派。国家级的戏剧学院,国家投入这么多钱,学生考进来这么不容易,更应首先为主流戏剧培养人才,不宜沉溺于自娱自乐的先锋花样。学生来专业院校要学好技艺,这样才能吸引观众自愿买票来看他们的戏。戏剧界我很佩服的老先生刘厚生说:“戏剧一定要有保留剧目。”这个道理哪儿都一样。好剧团理应有保留剧目,就不用一年四季编新戏,做一个扔一个。等我们主流戏剧发展好了,人均戏剧量提高了,老百姓习惯了自发买票看戏,如果还有余力,再去着力开发边缘戏剧,探索我们自己的先锋派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希腊悲剧在近现代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5BWW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